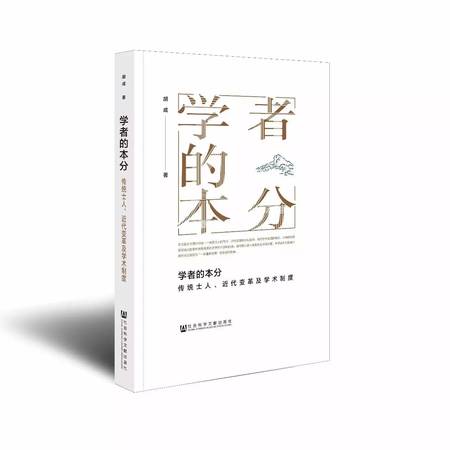胡成:“世间已无陈独秀”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7-07-25
“作为思想的先驱,陈独秀以其大刀阔斧之力,冲荡和振刷了国人一切黄茅白苇之习,使思想精神顿换一新天地;作为学术的重镇,陈寅恪以其筚路蓝缕之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在他们两人之后,中国学术思想岂能再局促自缩,自诧升平之象,而糜天下于无实之虚文乎?”作者在文中比较了陈寅恪与陈独秀对近代学术思想界产生的影响。本文出自新书《学者的本分——传统士人、近代变革及学术制度》。胡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时代精神的嬗变兴递几乎都以一种震荡和摇摆的方式,并体现在世纪之交的起伏跌宕之中。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切换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由渐进改良转向激进革命。悲慨泣血,危亡痛觉;鼓吹解放,诋斥弊政;可以说是这一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思想主题。不过,逮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转换似乎在于平息多年持续不断的喧嚣与浮躁,开始转向平静和沉思,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传统复归和文化建设,而不是昔日引以为荣的所谓陈涉、吴广式之文化破坏和文化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只是在专业范围内被人了解、被人敬重的陈寅恪,也从文史的圈子推向了整个学术界,几乎成为今天中国文化中最受人尊礼的一个精神象征。
陈寅恪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和文化巨擘,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继往,还应开来。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君子之道,弘传奕世,非徒以迹美而名高。而且,陈寅恪自己也有相关的认识。一九五一年,他在所著《论韩愈》一文中指出,韩愈之所以在唐代文化史上有一特殊地位,还因其特具承前启后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以致“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学者不绝于世”。当然,观陈寅恪终生运命,恰如他浩叹的“天其废我是耶非”,一生屯蹇之日多,安舒之日少。尤其是在他晚年失明之后,继以膑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其时,门下之寥落孤寂,身边助手只有几位巾帼女性。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请女助手写篇论及自己研究方法的文章,最终却未能如愿,耐人寻味的是,当女助手很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大师则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其中的深切痛楚——究竟是对现实境遇的无奈,抑或意识到自己学术身后无人的绝望,实在令后人难以知晓。
有学者明确写到,即使今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可能再出现一个在博学和天资上能与陈寅恪相埒的奇才,但由于近代中国那个新旧文化空前未有的冲突已一去不再,陈寅恪一生悲剧构成的文化意象犹如夕阳残照中历经兵燹的圆明园的断柱,就具有了一种永恒苍凉的审美价值。尤其是时下那些鲜有传统德性的人却在高倡文化道统,由此似可断言:“文化巨人陈寅恪构建的文化意象也将是永远绝后的。”与今天相比,那个已逝去的时代倒可说百家争鸣、大师迭出,陈寅恪并非独一无二。具体言之,即使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还有为文化衰亡而自沉于昆明湖的王国维;再从学术思想的演化来看,刚柔相摩,互为激荡,在思想另一极的还有全盘肯定西方近代文明、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独秀。
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标准言之,陈独秀在记诵名数、搜剔遗逸,即学术研究的各个具体问题方面,建树不多。一九一七年,蔡元培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出掌中国最高学府之文科,北大一些教授就以他学无专长、只写些策论式的时文而反对这一任命。后来蔡元培以其精通训诂音韵,并举出他有相关的文字学著作,终使风波渐渐平息。但那些文字学研究,如二十年代由上海亚东书局出版的《字义类例》,作为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却是因为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被倪嗣冲追捕而蛰居上海时的杜门之作。以后的一些相关著作,包括三十年代初撰写的《中国音韵学》《连语汇编》及最终没有完稿的《小学识字课本》等,也都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排斥、被批判,至被诬陷的不得已之作。学术上的价值,可能如梁实秋所言,他只不过用科学方法将文字重新分类和以新的观点解释若干文字的意义,使内容简明扼要,易于了解。
作为思想界一时的领袖和新文化运动之主将,陈独秀却是以中西学术作为其思想的根基。陈独秀虽以极轻蔑的语气提及自己考中的“八股秀才”是用不通的文章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但自幼熟读经史,之后读《昭明文选》渐渐读出味道,其诗作思想高,气体称,胎息厚,颇有宋人气象,应当说“旧学”功底还是不错的。再至留学日本期间,他研习日文,并能用英文、法文看书;同时撰文介绍欧洲文学思潮,还与苏曼殊一起翻译英诗。据章士钊说,《神州日报》所载《论欧洲文学》等论文都是陈氏的作品。实际情况可能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非其心志所在,他矢志以求的是在思想层面上的扫霾拨雾,摧陷廓清。至于日常生活,更不是他的关心之所在。一九一四年,陈独秀曾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一天早上,章士钊见黑色衣衫满是星星白物,骇然曰:“仲甫!是为何也?”他则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
一九一四年,他首次用“独秀”笔名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针对当时风行的爱国主义,提出“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而遭人詈非。虽则李大钊说,读陈独秀之文,伤心不已,“有国如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更无不情智具穷”,这表明陈独秀所持的正是一种不愿与那些恶制度共立,则宁愿与之偕亡的极端心态,然而,就“五四”全盘反传统思潮来看,陈独秀的鼓吹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处在这一激进思潮的另一端是后来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所说的:“劫尽变穷,则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陈独秀的激扬蹈厉,并非只是陈寅恪严正忠实的反衬,两人的精神或许也有同大于异的地方。一方面,纵观二十世纪初这一学术思想发展、陈独秀鼓吹新文化运动产生思想影响的时期,陈寅恪还在欧美游学。其时,袁世凯尊孔读经,实欲以帝制自为。所以,陈独秀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中国文化,不是认为儒术孔道没有优点,而是强调其施之于现代社会,缺点正多。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礼教、生活、政治,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于焉,故难与现代个人独立主义相融合。
同样,陈寅恪回国以后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之时,虽然袁世凯意义上的尊孔读经早已被中止,但统治者们几乎都在礼义廉耻的层面上露骨或隐晦地提倡和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贯穿陈寅恪终生的,是维护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早年,他在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思想若不自由,毋宁死耳。”五十年代的《论再生缘》又指出,六朝及宋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同时还称道端生对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的君夫三纲,皆以摧破之。他说:“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警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晚年陈寅恪更是竭尽十年心血撰写《柳如是别传》,大力彰扬体现在那些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身上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
另一方面,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继学术觉悟、政治觉悟之后,已进入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出自他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强调的启蒙,实际上是刻意再造新时代社会伦理。因为在此之前,陈独秀就意识到今天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新文化运动开创之时,他在《新青年》中提出新的时代精神应该是民主和科学,具体表述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寅恪似也有此思考。他一向认为,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逮至后来,遂若警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就如前述《柳如是别传》,虽是他研究明清之际“红妆”的身世之著作,却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著有深意存焉。陈寅恪终生服膺宋儒欧阳修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力,崇尚气节,遂一医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由是,孰不谓二人不是百虑一致,异轸同归?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向来存在着两个最为深刻的主题:一个是破坏,另一个就是建设。如梁启超所言,古今建设之伟业,莫不含有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再就两人精神指向而言,陈独秀之时,中国精神困顿委琐已久,所以他宁愿甘冒全国学究之大不韪,高张“文学革命”大旗,将胡适最早作为“文学改良”、所修也仅“八事”的通讯讨论,提高到关系文化兴废、民族生存的思想斗争。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虽然容纳异议、自由讨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但唯独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说,是非甚明,“必不容为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寅恪之时,新文化在某些方面已如梅光迪所言,“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职是之故,陈寅恪坚持中国文化已不像与其识趣特契的王国维那样——理智是现代,情感却是古代;而是自我定位在“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并致力于中西文化的切实融合。在他看来,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其真能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在上述意义上,两人又可谓分途赴功,交相为用:作为思想的先驱,陈独秀以其大刀阔斧之力,冲荡和振刷了国人一切黄茅白苇之习,使思想精神顿换一新天地;作为学术的重镇,陈寅恪以其筚路蓝缕之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在他们两人之后,中国学术思想岂能再局促自缩,自诧升平之象,而糜天下于无实之虚文乎?
再从当时特定的历史场景而言,身处旧邦新命之际,恪守一种精神价值又远比推进一种学术研究更为艰难。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短稿》中所言:“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盛,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环境而已。”当然,对于陈寅恪来说,精神之弘毅,绝不随时俗而转移,确可认为“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衿,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本来,自志于立言不朽之域,持短笔,照孤灯,未尝一籍时会毫末之助,可能就是不可改变的恒常境遇。然对于陈独秀,则完全可以是另一种生活。王森然先生说,那些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诸人,当时或居政治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陈独秀之学力,“苟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事实上,陈独秀晚年孤冷,惟同两三失意之人,相与论文以慰寂寞而已。
陈独秀的困厄与性格的过于清高有关。据说,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生活非常窘迫,常常要进当铺。他的学生,时为国民党显要人物的罗家伦、傅斯年送来钱款,但都被拒绝。他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财去,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更重要的还是他在自己认定的价值原则方面从不妥协。对他而言,这一价值原则是说老实话,所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来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押往南京监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特殊关押,国民党显要何应钦赴监狱探望,请他写字,得到的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在法庭上章士钊为他辩护,说其不反对国民政府,他则当场起来声明:本人的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出狱之后,虽然正值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合作之时,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些时日,但为未来中国考虑,他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社会主义不应排斥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成果。陈独秀一度也曾为时代的明星,登高一呼,从者如云,历史最终跨越了那个年代。与之相应,很自然的就是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被淡忘和被搁置。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史上,宽于责人,严于责君子,这种求全之毁,极易造成一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混沌世界。毕竟,学术和功业,言论和行事,都可以比较衡量,并随时而兴亡,唯有其中更为长远的文化精神,才真正不会被时间磨蚀而消亡。套用陈寅恪在王国维碑铭中的一段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光”。由此,学术思想的发展就不是简单的线性进步。那些真正感受到一种文化衰落之时的苦痛并为之憔悴的历史人物,对后人来说,既不是被挟之以自重的文化偶像,也不是诋之以鸣高的过时英雄,而是力求在一个科学与民主意义上与其神理相接。否则,倘若“世间已无陈寅恪”,那么世间也一定不会再有陈独秀。
推荐阅读>>>
学者的本分:传统士人、近代变革及学术制度
胡成 著
2017年7月
本文集由三部分组成——传统士人的气节、近代变革的文化坚持、现代学术制度的确立。全书的旨趣是想借此反思如何维系现代大学的宁静和自由,如何能让学人有更多从容和淡定,并尽最大可能减少将学术生涯视为“一场鲁莽赌博”的紧张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