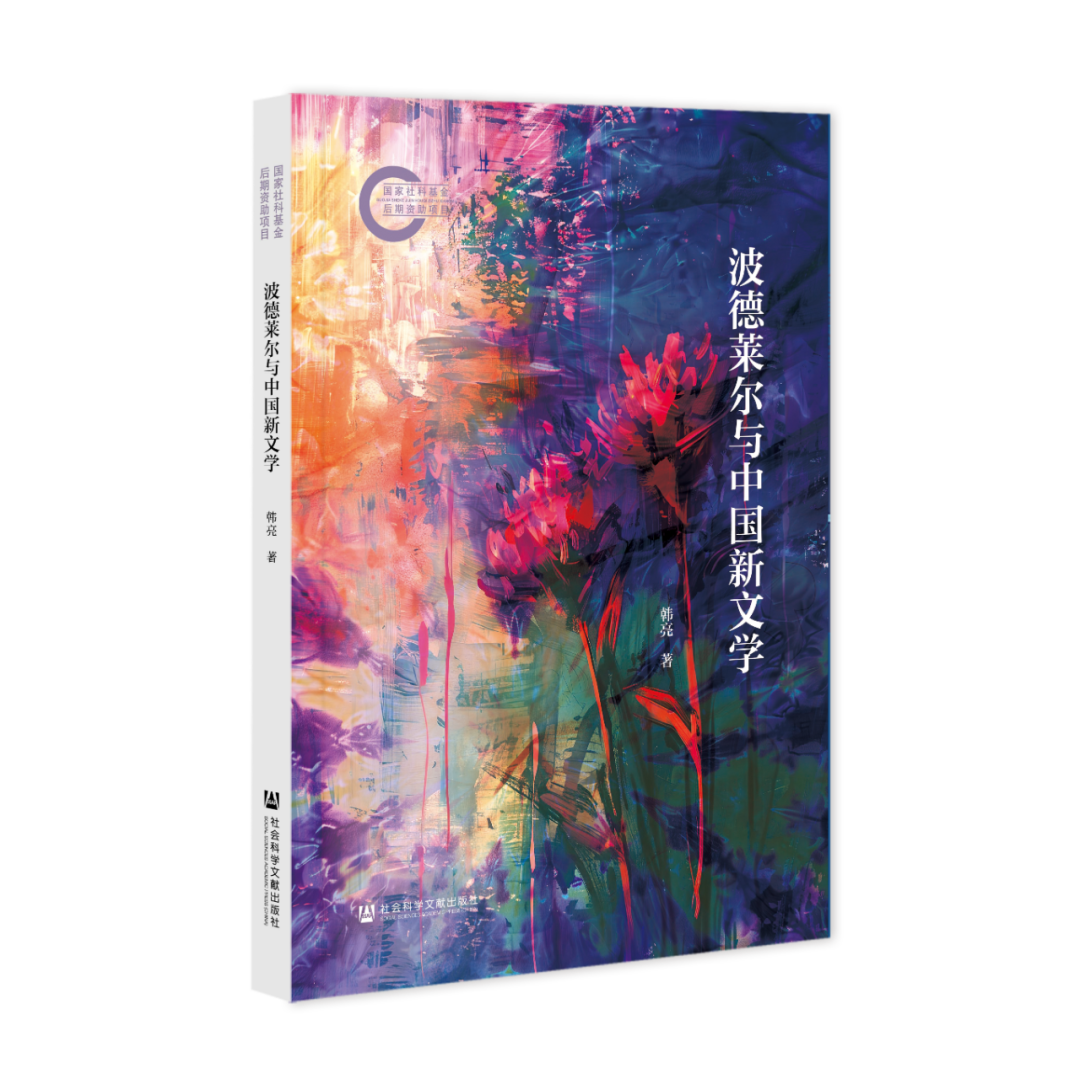新书 | 《波德莱尔与中国新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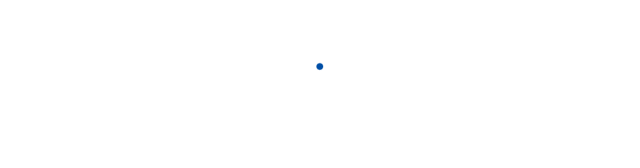
作为19世纪象征主义诗歌先驱,夏尔·波德莱尔以《恶之花》的惊世骇俗与《巴黎的忧郁》的形式革命在法国文学史刻下永恒印记,其诗学理念更如暗夜灯塔般辐射全球。自1915年被引入中国,这位“恶魔诗人”开启了百年跨文化旅程,他既是中译本最丰的法国诗人,也是深度参与中国新文学变革的域外诗魂。这引发我们的双重叩问: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波德莱尔的诗学何以突破文化屏障形成超时空对话?中国作家又如何将其美学基因融入汉语诗学体系?
《波德莱尔与中国新文学》突破传统影响研究的单向度模式,通过系统梳理百年来波德莱尔在中国的译介谱系、传播轨迹与阐释维度,完整构建其“中国化”的立体图景,特别揭示了中国作家在接受过程中展现的主体性智慧——他们并非被动移植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是将其嫁接于汉语诗学的根系,催生出兼具现代意识与东方韵味的文学新质。这项跨越时空的诗学对话研究,为理解20世纪中外文学交互影响提供了具有范式意义的个案。
走向一种新接受史研究
(绪论 节选)
法国学者让·克莱尔在《艺术家的责任》一书中说道:“精神流派、思想运动、形式变迁走的不是纯天然的天路。它们是地面的支流,曲折、迂回、阻滞、回流,遭遇种种阻力;任何意外都能截断它们,或因此改变流向,就像游人们不期遇河临渊,闯进森林。在这一领域,不能省掉丁点地面的意外。相反,正是这些意外本身使思想成为历史,凹凸起伏、摩擦不断却深富意义。”这段本是针对法国先锋派艺术做出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有关中国新诗对波德莱尔接受状况的贴切描述。在我们看来,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国知识界对于波德莱尔及其作品的接受是否准确,或是学习的水平高下,而是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分析那些绝不仅仅是出自偶然的“意外”,梳理那些看似无意识的选择、仿佛出于无知的误用,观看其中是否存在什么新文学自我成长过程中内部或外部的原因。这些错误与意外事实上都成为中国新诗自身的历史,也是思想史的一种特殊表征。这也就构成了我们计划中“接受误差”研究的主体。当然,中国文坛对波德莱尔的接受并非任何时候都存在误差,“接受误差”研究的提出只是为了针对其中遭到“双重误解”的材料和现象,并不代表我们要将这一方法无限扩展到波德莱尔接受研究的整个领域,比如对于20年代,我们就会着重论述顺承式的接受情况。这与我们对三四十年代的许多问题进行的“接受误差”研究并不构成任何矛盾。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使用了“误差”一词,但我们并没有赋予该词语任何贬义,也无意从是非高下的角度扬西抑中,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将接受过程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与差异重新转化为有意义的材料和线索,并对接受方也就是中国文坛展开全面的审视。同时,借助外部的参照系,还可以挖掘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易直接察觉的某些线索。而运用这一研究方法,首先要对接受研究中现有的“挑战—回应”模型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
毋庸置疑,“挑战—回应”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研究的通行模式,必然由于在很大范围内有它的适用性。譬如在法国19世纪诗歌史中,浪漫派的拉马丁认为诗歌应该登上希腊众神所在的帕尔纳斯山,而勒贡特·德·李勒则针对拉马丁的观点提出诗歌要走下帕尔纳斯山。后者反感浪漫派过于充沛的激情,认为写作应该客观冷静。那么,在李勒与拉马丁之间,或者说在帕尔纳斯派与浪漫派之间,这种“挑战—回应”的关系是完全成立的,也正是在挑战的过程中,帕尔纳斯派逐渐在诗坛取代了浪漫派的主导地位,法国文学史中类似的现象在后来的帕尔纳斯派与象征主义之间、在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之间反复上演。从国与国之间来说,在德国浪漫派与法国浪漫派之间、在拜伦的《唐璜》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间、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小说与法国小说之间,后者对前者都非常熟悉,继而形成了明显的挑战与竞争关系,并使“挑战—回应”成为西方学者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所广泛采用的模型。甚至在中国文学内部,在唐诗与宋诗之间、在宋词与清词之间、在古典文学与新文学之间,“挑战—回应”的关系也是广泛存在的。然而,在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学冲击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中国新文学之间,我们认为这一模型在很多时候并不适用。试举一例,很难认为李金发试图以他的诗作挑战波德莱尔或挑战魏尔伦,李金发更多的只是学习者、模仿者,波德莱尔、魏尔伦是他的启示者与可资利用的文学图腾,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挑战—回应”的关系,他利用波德莱尔、魏尔伦等西方典范诗人的身份符号去挑战其他中国文坛上的诗人与作家,为自己不合群、无先例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正名。李金发既不想挑战波德莱尔,也没有任何需要对其加以回应之处,他更多的是将波德莱尔当作自己的模范与护符。这样的情况并非现代文学史上的孤例。此外,“挑战—回应”必然发生在两个健全的文学主体之间,尽管会有代际先后,但挑战者/回应者必须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与被挑战者/被回应者构成成年人之间的游戏。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说,从新文化运动开始,面对古典文化,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从一开始就具备一种主体意识,即求新、求变,去创造一种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文学、不一样的文化,并以此向传统发起挑战,于是产生了白话文运动及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整个新文学大厦。在古典文学与新文学之间,后者对前者的否定性态度构成了它鲜明的主体性。所以,面对传统,以颠覆者姿态出现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一个强大的否定性主体,并从对传统的否定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出路。胡适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把之前提出的“八不主义”改作肯定的语气,重新提出了四条意见:有话说的时候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说自己的话,说本时代的话。可以发现,胡适提出的这四条肯定性的意见其实是对他本人“八不主义”的反向总结,套用尼采在“精神的三种变形”中使用的寓言就是:“攫取自由”的狮子代替了“负重”的骆驼,但离“建立新价值”的孩子的出现还有距离。尼采说道:
创造新的价值——就是狮子也还不能胜任;可是为自己创造自由以便从事新的创造——这是狮子的大力能够做到的。
给自己创造自由,甚至对应当去做的义务说出神圣的“否”字,我的兄弟们,在这方面就需要狮子。
要获得建立新价值的权利——对于负重而怀有敬畏心的精神,乃是最可怕的行动。确实,对于精神说来,这无异于劫掠,这乃是进行劫掠的猛兽的行径。
…………
可是,我的兄弟们,请回答:连狮子都无能为力的,孩子又怎能办到呢?进行劫掠的狮子,为什么必须变为孩子呢?
孩子是纯洁,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
胡适就仿佛尼采笔下的狮子,他打破了重负,创造了自由,获得了“建立新价值的权利”,但新价值的真正建立狮子无法完成,而有赖于孩子“神圣的肯定”。在整个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过程中,“狮子”从一开始就占有醒目的地位,而“孩子”的形成则相对显得缓慢和谨慎。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做出更多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在此无意进一步展开,只是想从这个角度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新文学的主体身份在发生阶段同时具有双面性,它虽然拥有一个明确的否定性主体,但尚不具备一个完整的肯定性主体。换句话说,新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知道要破坏什么,但对于建设的设想却基本来源于对破坏对象的逆反,新文学除了在大方向上要成为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东西之外,具体如何创作还要在实践中探索,更具原发性的自觉意识也要在探索中逐渐形成,于是一切都要从胡适式的“尝试”开始。中国本土的象征主义诗歌运动时期的理论建设虽然相比胡适时期体现出更多的肯定因素,但在本质上依然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19世纪的法国诗歌,或者说面对广义的西方思潮,由于脱离了古典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否定逻辑,诞生与成长中的中国文学对西方思潮的挑战意识其实是非常微弱甚至几乎不存在的。此时期的中国新文学面对西方思潮还处在学习和自我寻找阶段,没有也不需要成为一个质询者向西方文学发起挑战,更多的是好奇地寻找、打量那块“他山之石”,兼容并蓄,从各类流派与思想中取己所需,然后为己所用,最终“打破传统”,“成为自己”。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诗学对外来文学的接受过程中,其终极目的总是指向自身的,与外来文学之间不形成竞争关系,当时的作家对外来文学做出的反应在事实上也始终基于新文学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特定需要。如王独清在《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中所说:“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我觉得有倡Poesie pure的必要。——木天!如你所主张的‘诗的统一性’和‘诗的持续性’,我怕也只有Poèsie pure才可以表现充足……以异于常人的趣味制出的诗,才是‘纯粹的诗’。Baudelaire底精神,我以为便是真正诗人底精神……我望我们多下苦工夫,努力于艺术的完成,学Baudelaire,学Verlaine,学Rimbaud,做个唯美的诗人罢!”无论是“纯诗”的概念还是波德莱尔、兰波,在此都不是被挑战者,王独清所期望的也不是挑战或者回答什么,而只是获得灵感、学习取法,从而去完善自身。从周作人1919年第一次在《新青年》上论及波德莱尔开始,其目的就是通过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学寻找新方向。包括鲁迅1930年在《萌芽月刊》上对波德莱尔的批评,其真实意图也是指责当时中国文坛上他难以认可的写作风气,以此表示新文学的未来应该另寻出路。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范围内讨论波德莱尔(以及同时期许多外国作家与流派)的中国接受问题,“挑战—回应”模型不是有所“不足”或者需要修正,而是在本质上难以适用。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吸收/改写—成长”模型,这就是说,关注中国文坛如何将波德莱尔的诗学和美学因素化为己用,自我成长(“吸收—成长”),以及在另一种情况下,中国接受者又如何在特定语境中重构波德莱尔的形象,赋予他与法国原型相比不同的“标签”,从而使中国的诗人作家得以完成他们自身的文学成长与身份构建(“改写—成长”)。这一重构过程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主动过程与被动过程:所谓主动过程是指作家主动地刻意误读,其中必然包含该作家自我成长的明确意识;所谓被动过程则是指作家在阅读过程中不经意形成的误会,于是从反方向暴露出他一贯的文学观念与主张。总而言之,通过“吸收/改写—成长”模型,把重心从中西之间转到以中国为主的方向上,从“挑战—回应”的对抗关系转到以自身发展为主线的角度上,从而在接受研究中真正展开对中国文学主体自觉性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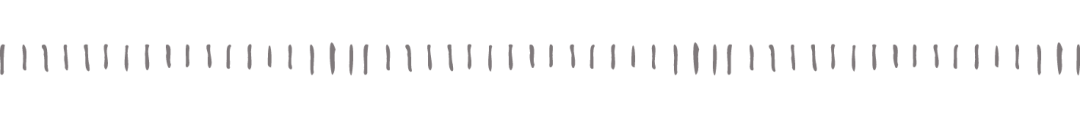
书籍信息
波德莱尔与中国新文学
韩亮 著
2025年5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5286-7
作者简介
韩亮,1986年生,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中文教育系副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研究,关注诗歌的跨文化传播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建构。担任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秘书长、理事,并入选江苏省第七期“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333工程),获江苏省首批华文教育专家称号。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学术成果曾获江苏省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二届江苏省紫金文艺评论奖、南京大学“育教融合奖”等。
书籍目录
( 上下滑动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