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林业的生成:近代中国东北的森林治理与产业秩序(1860~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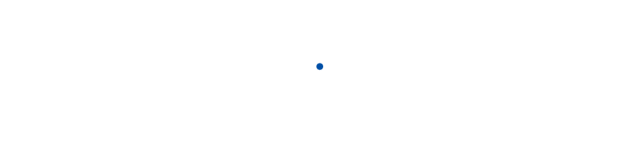
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产业化利用是近代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治理水平和发展潜力,也影响着普通民众的身份认同与生活秩序。《林业的生成:近代中国东北的森林治理与产业秩序(1860~1931)》以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资源利用与产业秩序为主要议题,尝试将该地区的林业问题置于跨国史和近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整体脉络中进行多元、立体、综合的考察。本书通过探讨近代中国东北森林产业化的思想资源、制度设计、利益冲突、机构运作、权属纠纷、市场秩序等内容,思考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外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森林治理与产权嬗变、边疆危机与国家转型之间的复杂互动和深远影响,重新审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国家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大范围内国家动员、资源治理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

序
仲伟民
森林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林业既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保障,也是环境保护的最主要资源。但从先人的历史记忆中,我感受到中国人对森林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和恐惧感,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森林的排斥。诸如将犯人流放到边疆林地,以及对西南地区瘴瘟、东北地区严寒的恐惧,大约就是中国人对森林最为深刻的印象了。究其原因,无疑是原始森林远离人类文明核心区域,森林地带由此就成了野蛮的代名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在中国人看来,耕地才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区域的扩展密切相关,这几乎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主调。当然也不容否认,中国人尽管经常把森林看作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瘴瘟之地,但仍然认为森林是农耕文明扩展的必要空间。中国人对森林的认知,大致如此。
所以,一部中华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也大致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国森林消失的历史。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极端,但是如果从林业史的视角思考中华文明史,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森林资源贫乏的国家,到帝制中国的后期,这一点愈来愈突出,甚至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正因此,近年林业史研究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大增长点,可以说林业史研究对丰富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的林业史研究,大多集中于环境史、山林产权、林木买卖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也有一定局限。池翔的这部著作,因为关注的主题、区位、时代等都非常特殊,所以她思考的问题也更加重要、更加广泛、更加特殊。她跳出林业史、环境史、产权史的传统研究范畴,从全球史、知识史以及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等方面,来探讨东北林业及相关的重要问题,观点新颖,眼光敏锐,方法独特,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

冬天的大兴安岭(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
首先,本书从跨国史或全球史的视角展开对中国东北的研究。
如果读者认为本书是关于中国东北地方史的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东北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域,近年关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但本书作者眼光高远,没有就东北谈东北。也正因如此,本书可称为从东北出发的跨国史或全球史。在清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东北的特殊性非常突出:清代前期,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被执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这使它在清代大部分时间内成为一个神秘的存在。东北封禁的结果,是中国有了面积最大的森林景观,但客观上也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施坚雅在划分清代中国经济区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说,东北不可与中国的其他传统经济区相提并论。晚清以后,东北才成为中国较为重要的经济区。更需要注意的是,东北封禁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使对领土无限贪婪的沙俄乘虚而入,中国外兴安岭大片地区的丢失,与清政府的长期封禁政策关系极大。东北地区的复杂性,直接由清朝的封禁政策引起。1860年后,东北地区逐渐开禁,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沙俄的继续渗透。所以,此时东北的问题,已经不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跨国史的重要问题,甚至是国际性或全球性的问题。可惜,清政府的醒悟太晚,因为到19世纪晚期,不仅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极具扩张性的沙俄,东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且同样具有侵略性的日本,此外还有欧洲列强的觊觎。尤其是沙俄及日本都把中国东北作为自己志在必得的势力范围,使晚清及民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地区进行完整的统治和管理。这是研究晚清以来东北历史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大背景。本书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论述,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复杂且丰满的东北史。

长白山林区秋季茂密林海晨雾(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
其次,本书从知识史的视角审察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能源从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矿物能源被人类充分利用之前,森林资源的重要性可以说首屈一指。也就是说,林业与现代化关系密切,在很多地区林业甚至直接为初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但在东方人的观念里,林业从来都是被纳入农业体系的,中国人只有“种树”的观念,没有林业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中,林业是缺失的。当然,即使在西方,林业也同样经过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国人林业观念的缺乏,与传统的农本观念密切相关。即使到了20世纪初现代化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立国最强音的时候,林业依然很少被纳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人的林业知识主要来源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向欧洲学习,大约因为日本资源的极度缺乏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日本人逐渐提高对林业重要性的认识,后来远超他们的欧洲老师。从明治维新开始,林业不仅逐渐被日本人认为是文明国家的事业,而且还被认为是“永续的”事业,是国家工业实力的基石。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日本对林业的高度重视,日本林学家甚至将“林业”视为日本在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把林业和进步、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时期的日本特别重视林业殖民。日本学者及政客普遍认为中国东北的森林对于缺乏资源的日本来说特别重要,应该将东北森林“收入囊中”。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经营,与日本人现代林业观念的形成不无关系。甲午战后,中国人大批留学日本,促成了中国人现代林业知识的形成。不同的是,日本人的林业知识更多与军事化、工业化、现代化相关联,而中国人的林业知识则更多与“造林治水”、发展农业的传统观念相结合。从中日两国林业知识史的建构,可以看出两国当时发展的实际差距以及知识人的不同追求。

黑龙江小兴安岭的林场(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
最后,本书从现代国家的建构审视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清朝前后期对东北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政策,使东北形势错综复杂,成为晚清民国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难点。清朝前期,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有多重目的,第一是要将东北的森林塑造为自身权威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手段,并借以维系满人的特殊地位和文化象征;第二,一旦满族建立的清政权有不测,他们可以退回“老家”。不承想,长达两百多年的封禁政策,不仅使大片领土落入沙俄手中,也让后起的东邻日本垂涎三尺,这个结果是清初的统治者无论如何想不到的。1860年后清政府逐渐开禁,允许内地汉人进入东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部分起到了防止沙俄及日本进一步渗透的作用。但是,这个时期东北开禁未久,尤其是政府很少介入林业开发及农业垦殖,主要还是靠民间自发的开拓和投资,因此对当地森林的开发和利用非常有限,弱小的民间资本始终无法与外国资本形成比较有力的竞争。在缺乏政府有效支持和规划的情况下,东北林业发展十分缓慢。尤其是晚清以降内忧外患频繁发生,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不仅东北地区的林业难以发展,而且这个地区的安全也难以保障。森林国有化的动议始于清末,具体实施则在1912年民国建立后。池翔研究后认为,民国初年东北的林业建设经历了集中化、专门化和国有化的改革,总体看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北洋政府在东北推行的国有林制度,具有深远意义,它既是抗衡外来殖民压力的策略,也是自上而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一环。尽管后来东北国有林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主体逐渐转移到东三省地方官署和各实业部门,但终究是强化了东北森林的领土主权性,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本书还对东北地区复杂的土地产权和森林产权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对东北林木市场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做了精彩的阐发;东北地区林地分离的制度设计丰富了我们的产权知识,也使我们对东北经济结构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的林业建设开始于东北,中国的林业史知识建构同样是在东北森林的开发中完成的。清末民初,国家开始强力介入森林资源的直接管理,而东北地区的“国有林”政策更是拉开了近代中国国家林业的全新篇章。本书不仅使我们对晚清和民国以来的东北地区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填补了我们许多关于林业知识的盲点。总之,池翔这部著作以国家与森林的互动为主题,聚焦近代东北林业的变革历程,既展现了中国林业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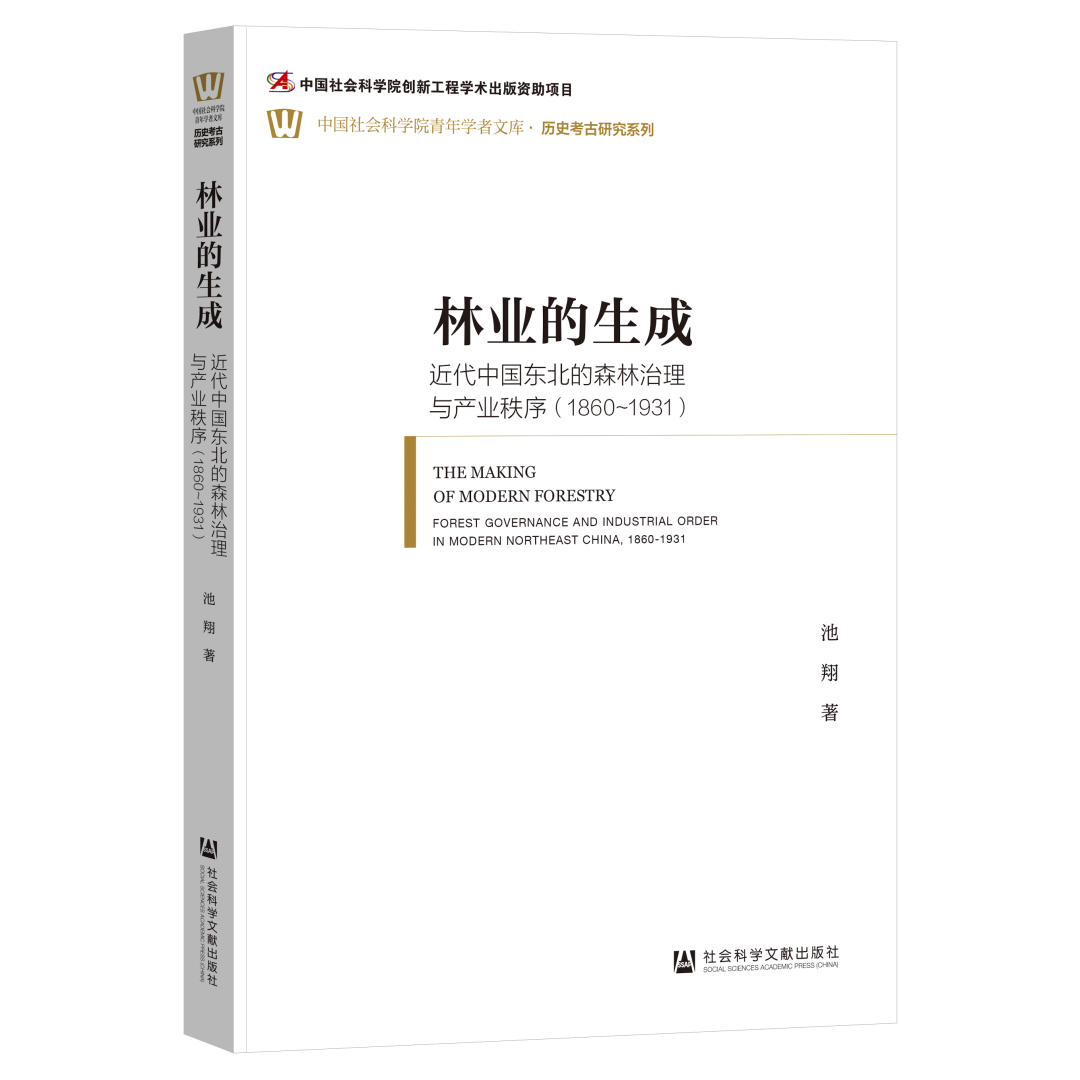
林业的生成:近代中国东北的森林治理与产业秩序(1860~1931)
池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作者简介
池翔,重庆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环境史和东北区域史,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
目录
编辑:周畅
审校:宋荣欣 李丽丽
转载自: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