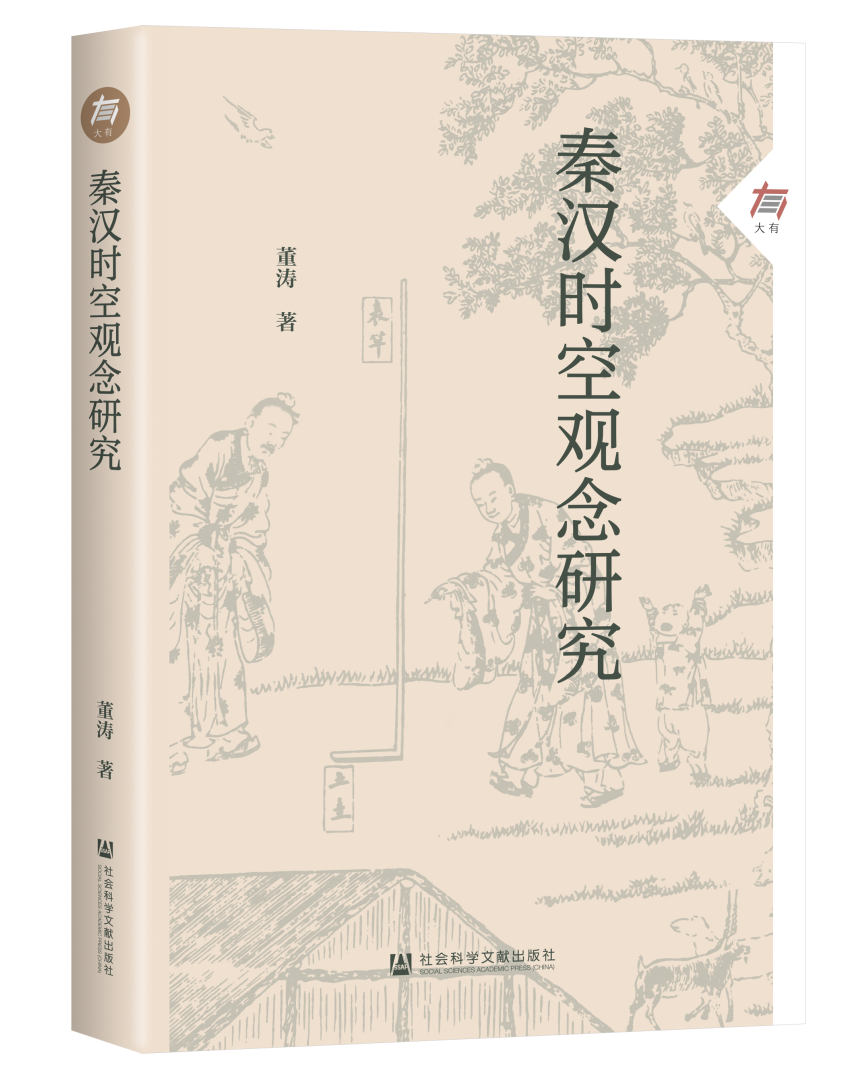新书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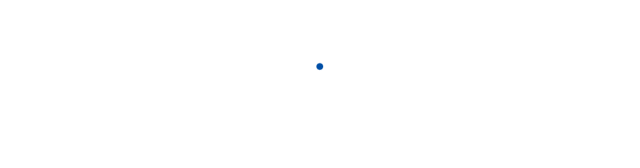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通过对时空测量工具的研究,探讨秦汉时代的时空观念。为了确定时间与空间,古人发明了多种测量工具,包括规矩、准绳,以及圭表、浑仪、漏刻等。进入战国秦汉时期以后,这些仪器的设计和制作都逐渐成熟,除了部分仪器仍然具有神秘功能之外,其他多数仪器已逐渐走向实用,在历法修订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有赖于时空测量工具的发展,人们思想中的理性因素逐渐加强,而其深远之影响,显然又不仅限于时间和空间观念方面。
序
李禹阶
时空观念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和认识,也是人们认知宇宙、自然的一种最为通常、普遍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当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农业和农业定居聚落时,对幽深玄妙的时空进行探索就成为原始先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于时空对古代人生产、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对它的探讨,既构成早期人类以天文学为主体的科学技术体系,也在历史演进中形成早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这在古代中国亦是如此。史前中国先民对天人关系和宇宙、方位的认知,大都与时空观念有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使史前先民往往将观测天象、物候等作为其时最重要的生存手段,并通过观天测地而实现对宇宙、时空的认知。从先秦到秦汉,中国古代时空观念及相关科学技术相互促进、长足发展,既提升了古代中国人对时空、宇宙的认知水平,也奠定了与这种时空、宇宙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的基础,使中国古代文化、科技呈现出鲜明特色。因此,研究先秦、秦汉的时空、宇宙观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董涛所著《秦汉时空观念研究》一书,正是通过对秦汉时人的时空观念的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并阐释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对我们深入认识秦汉时期的时空观及相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从人类历史演进看,最初的原始农业的产生,促进了以时空为主轴的原始天文学、农学等的萌芽和发展。原始农业是早期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革命,它创造的人工栽培的生产方式,不仅为史前人类的食物来源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人类的定居生活及社会组织的建立、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支撑最初的原始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就是原始天文学,这是因为人工栽培的原始农业需要有精确的时间观念,即对历法、节气、气象的掌握,这直接关系到人工栽培作物的收成及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例如错过了农时,那么农作物的歉收就会造成先民的生存危机。同时,早期人类的诸多政治、军事、生产活动,也离不开对气候、环境的了解。因此,在人类最古典的科技中,以时空为主要对象的天文学始终是人类最重要的科技门类,也是早期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书内插图:江苏仪征石碑村圭表
图片来源:冯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第321页。
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早期天文学伴随着史前先民的生产、生活而一同发展。从考古资料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后的聚落遗址就发现了原始天文学遗迹。例如在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发现如龟甲、骨笛、叉形器成组出现的随葬品;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如玉珏、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以及钻孔圆蚌等“神器”;在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下层,发现距今7000年前后的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和39个排列规律的祭祀坑,在出土陶器上发现了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八角星纹及其组合图案,显然它们既属于祭器一类,也是其时先民太阳神崇拜的写照。从大量人类学材料看,这种太阳神崇拜遗迹,主要来自史前先民基于生存条件而对早期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等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但是在史前,这种公共服务产品往往是通过原始宗教的方式来获取的。例如史前宗教祭祀天地、神祇的祭坛等设施,就包含着观天测地、了解节气、预告风雨雷暴、驱邪祛病等诸般功能。所以,早期巫术所蕴含着的宗教与科学、迷幻与理性等内容,正是先民生产、生活所需求的各种实际功能的展现,在原始宗教的幕布下隐含着史前社会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上的诸多发明、创造。又例如距今8500—7800年前后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刻图像,查海遗址中发现的用碎石块堆塑出的一条长19.7米的“石龙”,距今7200—6400年前后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5件刻画有神兽纹天象图案(包括神兽太阳纹、神兽月相纹、神兽星辰纹等)的陶尊等,就证明了早期聚落中先民的宗教信仰较集中地体现在与天文、天象有关的观象授时或预卜吉凶上。再如古人常常谈到的“律管候气”“测量日影”等,也是一种原始的天文技术。冯时先生在谈到贾湖遗址出土骨笛时指出,“十二律在当时很可能已经产生,而22支骨笛就是迄今我们所知的以骨为管的最早的骨律”,而这种“律管候气”,就是最早观测天象、节气的一种研几探赜的技术手段。

书内插图:敦煌莫高窟 285 窟伏羲女娲图
图片来源:王元林:《伏羲女娲文化西渐的图像学试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37页。
《史记·历书》索引述赞曰:“历数之兴,其来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纪。推步天象,消息母子。……敬授之方,履端为美。”它说明了早期人们的时空观及相关的天文学、数学等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价值。《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周易正义》则曰:“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周易·贲卦·彖传》亦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正说明了早期天文学与文明起源、发展的关系。从世界古老文明的发展看,与时空观密切相关的天文学、数学等不仅是服务于早期先民社会的文化之源,也是早期国家公共职能的重要元素。例如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天文学就与早期国家的设官分职密切联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少皡氏以鸟名官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皡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杜注谓:“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孔疏曰:“历正,主治历数、正天时之官,故名其官为凤鸟氏也。”它说明早期的神祇、官职与天文、历法、节令等公共事务息息相关。《左传》昭公元年又记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意为高辛氏之子阏伯被迁于商丘,使其“主辰”,而“主辰”即是对辰星的观测、祭祀。辰星即大火星,大火星系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之心宿第二宿。对大火星观测、祭祀之官,也是观天象、测农时的官吏,亦称“火正”。《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火正”一职,既是祭祀之官,亦是观测、预报农业节气的民事之官,故而文献记其有“司地以属民”的民事职能。《史记·殷本纪》则有商族先祖契辅佐禹治水有功,舜命契为司徒(司土),“敬敷五教”的记载。故《史记·历书》载:“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它说明了时空观及相应的天文学知识,不仅在古代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在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秦汉时期的时空观及相关科学技术的探讨,无疑是有着较大难度的课题。严格来说,从先秦至秦汉的时空观是一个多学科问题。由于古代时空观及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大都遮掩在古代宗教的幕布下,因此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的探讨,也包括了古代宗教、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界域的诸种问题。“天人之际”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与时空观有密切关联的制历、星象、占卜,包括王朝改易的“正朔”等,在王朝历史上本身就呈现为一种“推本天元,顺承厥意”的政治文化。这种情形给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时空、宇宙及天文、数术等的探究增加了极大困难,它不仅要求学者具备丰富的历史、文献知识,也要求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古代宗教知识。因此,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该领域目前虽也有颇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长足发展相比,它仍然处于较薄弱的研究境地,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书内插图:汉武帝茂陵石圭
图片来源:王志杰:《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三秦出版社,2012,第93页。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一书,正是作者在这一领域寒耕暑耘、有所创获的一部作品。该书以秦汉天文、测度与计时仪器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中的天文仪器资料,而对秦汉时人的时空观、天人观等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该书重点探讨了历史早期的时空、天文测绘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对“规”“矩”“准”“绳”,以及土圭、圭表、璇玑、浑仪、漏刻等测绘计时工具的产生、发展、功能、运用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无疑使我们对秦汉的时空、天文观念及测绘、计时仪器有了新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该书还对隐藏在这些仪器、观念背后的科技知识及政治文化内涵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分析、研究,例如对规矩、准绳与时空、宇宙观念,璇玑、浑仪与星象模拟中的时空认知,漏刻与精确时间观念,以及威斗与时空模拟、政治斗争中的厌胜作用等的关联都做了爬梳、阐释,使我们能够知晓秦汉时期测绘仪器的功能、作用及时人时空观、宗教观的变化等。书中亦经由对天文、历法等古老的科学技术进行分析,将秦汉时人的时空观与“天人合一”“天人之际”的政治、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考察,进一步论述了秦汉时空、宇宙观念的宗教文化的特征。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根据星象制作的璇玑玉衡等天文仪器,并非单纯的测量工具,也蕴含了王朝统治者试图借助天文、星宿等宗教观念来维持人间的等级秩序的现实意图。为了更好发挥这种测量工具的作用,王朝统治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天象的简单模拟,而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通过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掌握建构起一种能够预知吉凶、防范禁忌等的宗教文化,这也是古代择日而行的思想基础。在统治者倡导下,秦汉民间社会此观念、手段亦甚为流行。所以,尽管看似是纯粹涉及自然科学的时空观念,但是当它加入了政治、宗教的内容,就成为秦汉时代普及的“天人相兼”的政治文化,并被统治者当作对秦汉社会进行整合、控制的工具。西汉末期这种情况甚著。作为汉家外戚的王莽夺取汉政权,出于内心恐惧,一直着意于通过天文、星象、占卜等观念、手段来厌胜其所取代的汉家神灵。王莽铸造威斗即是典型例证。威斗以“斗”为名,其基本形制来自北斗七星,并参考了作为量具的斗的形状。但是王莽铸造威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制作一种有效的天文测量仪器,而是为了厌胜前朝神灵和压制当时愈演愈烈的四方动乱。因为在王莽等人看来,王朝政治、社会规律和北斗七星在宇宙中的运动轨迹息息相关,这种关联性使北斗七星自然具有神秘的辟邪、祛魅功能。《汉书·王莽传》记此事曰:“是岁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这一段历史记述既形象地表现了天象、星宿运行与人间的帝王气象的关系,也证明了时人的“天人相和”、威斗厌胜的观念。因此,在对秦汉时期的时空观和测绘工具进行研究的同时,亦要注重隐藏在其背后的王朝政治文化及其变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秦汉时期的科技、文化及其与王朝政治的关系。

书内插图:铜方斗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正是这么一部颇具研究难度而又富有新意的学术著作。当然,该书仍有需要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书中对先秦时空观和天文、历法等对秦汉时空观念建构的影响的分析、探讨还显得薄弱,对秦汉时空观与秦汉大一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背景的有机联系等的探讨还略有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在秦汉政治史、科技史、宗教史等方面开启一扇新的窗户,以一种新视野来认识秦汉时期的政治、科技、宗教等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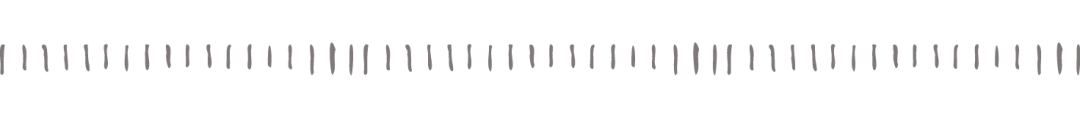
新书速递
(点击封面跳转至小程序购买)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
董涛 著
2024年12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28-1934-1
作者简介
董涛,1984年出生。2007年于西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4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秦汉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秦汉时空观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秦汉时期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等,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 上下滑动浏览 )
转载自: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