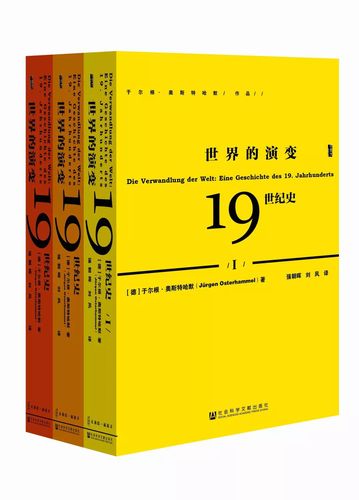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比印度成功丨专访奥斯特哈默
作者:强朝晖 刘风 来源:文化有腔调 时间:2018-08-22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从19世纪开始,人类现代史即将拉开序幕。这是一个重大政治理念汇聚的时代,是铁路与工业的时代,是各大陆之间的大规模移民以及首波经济和通信全球化浪潮的时代,是民族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时代。但同时,在今人眼中,19世纪却已变得遥远而陌生:一个辉煌的昨日世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从世界史的角度描绘和剖析了这段历史,一个欧亚美非各大洲经历剧变与全球化诞生的时代。他将历史事实写得跌宕起伏、抑扬顿挫,为读者呈现出关于复杂和混乱的19世纪的独到见解。
此书刚一出版就大获好评。《纽约书评》称,它是“后冷战时代一部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外交事务》杂志认为,这本书“凸显了西方,却用非西方民族和社会的生动画像避开了欧洲中心主义”。不少人也将奥斯特哈默与布罗代尔相提并论,比如作家乔纳森·施佩贝尔就将奥斯特哈默称为“有关19世纪的布罗代尔”。2016年,他因此书获2017年汤因比奖。
奥斯特哈默生于1952年,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德国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斯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他发表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包括《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后两本也均已由甲骨文引进出版)等。因为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他曾获德国史学家协会奖和德国最高学术奖——莱布尼茨奖(2010)。
围绕此书,腾讯文化通过邮件采访了奥斯特哈默。以下为采访内容。
避免用“进步”“落后”的概念去思考19世纪
腾讯文化:写《世界的演变》花了你多长时间?
奥斯特哈默:这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要想了解一个完整的世纪,一个人得用几十年去读各种文献。可以说,这套书的酝酿时间远远超过了写作本身。写作也不是一气呵成的,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如果把一再中断的大量写作时段加在一起,总共大约是六年。
腾讯文化:在普通读者看来,世界史是国别史或区域史的综合,在中国很有名的《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是如此。但《世界的演变》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正如你引用布罗代尔的一段话所描述的——“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将这些近邻关系、这些边界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变成一个整体”。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奥斯特哈默:首先,大家应当知道,我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人类通史,不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其他许多历史学者那样的作品。而且对这样一种囊括人类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历史的写作,我也不感兴趣。这类写作其实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带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推论式色彩——仅就远古史、古代史和考古学而言,人类对它们的科学认知就已经非常广博,而且这种认知的变化非常快,生活在近几个世纪的人,没人能全面了解这一切。所以这种长时间跨度的通史型写作总有缺憾,不可能面面俱到。
其次,我不喜欢“综合”这个词——如果它指的是自下而上、把特殊的和区域性的东西提升到普遍或全球性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历史写作是无趣的,从学术角度看也没有意义。我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应当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小故事,列举了很多非常具体直观的例子。
但同时,我也在努力不让它变成一块由碎石拼成的马赛克。我更感兴趣的是关联和解释。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家是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理想类型”,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世界史分析非常实用。分析的重要性远大于综合,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我这套书是针对大量单个主题的大量分析的一个关联性汇总。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世界史写作的最佳和唯一可行的方法。
腾讯文化:写《世界的演变》时,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吗?
奥斯特哈默:人们往往都会把外语问题看作一个巨大的障碍,有些人甚至认为,世界史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没人能看懂所有需要阅读的语言文字。但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棘手的困难。如果一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全球史中的某个专项课题,他自然要掌握这项研究所需要的各门语言,因为他首先要能看懂原始史料;然而,对一个从全面阐释的角度进行历史写作的人而言,他的工作不能主要依赖于史料,即使其撰写的只是一个国家——例如德国或中国——的百年史。因为其中涉及的史料实在太多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全部拿来,逐一钻研。因此,针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写作,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世界史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最优秀、最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用什么语言出版的。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英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即使是论述中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很大一部分也是用英语写成的。不过,在人文科学领域,真正重要的学术语言种类其实并不是很多。因此,世界史学家首先要掌握那些“大”的语言。
遗憾的是,我不会日语,西班牙语水平也很有限。但即使我懂,也很难在一个小小的德国大学城里找到用它们写的相关著作。大部分图书馆都找不到这些著作。
腾讯文化:有关19世纪的史料浩如烟海,你的选材原则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我注重的是不能只顾及那些“伟大的文明”。比如在19世纪,有很多社会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它们更多的是人类学而非历史学要面对的课题。但这些社会当然也是时代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腾讯文化:写作时,你是否曾提醒自己要避免掉入某些陷阱?
奥斯特哈默:是的。我极力避免落入的一个陷阱,是用“进步”和“落后”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这不是说进步不存在,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历史写作中最妙的那一根红线。
另一个要避免的陷阱,是从“世界霸权”的范畴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排第一、谁排第二,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并不太关心。
和印度相比,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甚至是成功的
腾讯文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你提到你的学术出身是“中国”。你是如何开始中国问题研究的?为什么?
奥斯特哈默:说来有些话长。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以平行或彼此关联的方式,研究世界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组织:中国和英帝国——在各大洲,英帝国曾经都有自己的地盘,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者;而中华帝国则是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政治体。我198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中英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
后来,美国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接替了英帝国的位置。在我眼中,中美关系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腾讯文化:你出版过几本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如《中国革命》《中国与世界社会》。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中国革命》这本小书是唯一以中国国内局势为主题的。篇幅比它长得多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则将中国的外交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完成。
如今,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作为大学教授,我没教过中国历史课,教的主要是欧洲史和国际关系史。
腾讯文化:研究“中国”的学术背景对你写作此书有帮助吗?在你看来,和其他世界史的中国部分相比,这套《世界的演变》的中国部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即使是对从事世界史写作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对某些地区的熟悉程度也总是会超过其他地区。2015年去世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Bayly)就是一位印度专家。一些人比较了我们两人有关19世纪的著作,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因为贝利是以印度为着眼点,而我是中国。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我的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我一直在书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一种贴近现实的比例关系。就19世纪而言,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历史。
或许你会说,中国在19世纪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对此我只能部分赞同。对国际关系来讲,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实力确实比较弱。但它并不是被动的。例如和印度相比,在某些方面,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甚至是成功的。另外,当时中国在国际上虽然弱小,但始终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它是全球最大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
腾讯文化:在书中《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一章,你特别谈到了帝国的凝聚力问题,也谈到直到现在中国依然维持了与其在帝国时代相当的版图,而奥斯曼、哈布斯堡、大英帝国都已不复存在。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持久力”?
奥斯特哈默: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帝国”的概念在今天往往是带有批评色彩的:帝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并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从这一意义上讲,用“帝国”来描述中国并不恰当。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与一般民族国家是有差别的——在德国,人们对“少数民族”没有概念。另外,朝贡体系也对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都(不无道理地)自视为一套由其自身制定的世界秩序的中心,一片被边缘地带包围的核心区。
“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
腾讯文化:在《世界的演变》中,你的选材常常让人感到惊讶,比如在《生活水平》一章,你对当时全球各处的餐馆做了细致描述,甚至包括1910年英国炸薯条的快餐店数量。这种常人难以留意的微小事件,为什么会在你的世界史书写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奥斯特哈默:我是1970年开始上大学的,当时在德国,社会史研究非常发达。198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的“日常生活史”,关注各种微小的事物。我觉得,这两类研究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
另外,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应该多了解一些人类学的知识。我不认为“微小”与“宏大”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在世界史书写中,我们也应当尽可能细致地去观察日常事件和“普通人”的生活经历。
腾讯文化:在书中,你不仅仅阐释了19世纪的种种变化,还时常将视线转移到现在,关照现实的色彩非常明显。你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奥斯特哈默: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关照现实”的反面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纯理论。但纯理论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是哲学家或许还有社会学家的任务。当然,理论与现实之间是有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的成就,正在于把两者彼此联系。
我想在“关照现实”之外再加一个词,就是“关照当下”。并非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从当下出发去进行思考的,他们也未必一定要这样做。不过我个人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告诉人们,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
腾讯文化:在《世界的演变》出版后,欧美学界很多人将你和布罗代尔做比较,甚至有人直接称你为“有关19世纪的布罗代尔”。你对此怎么看?你认为自己和布罗代尔的不同主要在哪里?
奥斯特哈默:把我的名字和布罗代尔相提并论,于我当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是说实话,这也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布罗代尔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大师,他写了三部重量级作品,其中两本堪称不朽的经典:一本是关于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另一本是关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
布罗代尔有很多独创的理论,而我却没有。另外,他还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政治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称得上是法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家。而我本人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没有在德国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如果读者有充裕的时间,不妨先读一读布罗代尔有关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论著(中国在书中也占了很大篇幅)。接下来,再读我这套关于19世纪的书。
腾讯文化:启蒙时代是你所钟爱的历史时期,我们在你的另一本书《亚洲的去魔化》中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你为什么特别钟爱这个时期?
奥斯特哈默: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20世纪去殖民化的问题,不过,最近我又重新回到了18世纪,因为我的《亚洲去魔化》一书将要翻译成英文。它的德文版是1988年出的,我要重新对它进行修订和完善。
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树立的一些标准,比如独立思考的义务、个性发展的权利、对异见者的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政治权力等等,在欧洲和世界都面临危机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逃避理性批评,这或许是启蒙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原则。
在许多领域里,启蒙思想已经变成了不言而喻的法则,特别是整个现代科学都建立在启蒙基础之上的。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启蒙仍然备受争议,要让人们接受这些原则,必须用无懈可击的理由去抗争。我认为,启蒙并不是“西方”的,它所提出的思想具有普世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都普遍适用。
腾讯文化:据你观察,近些年来,世界史写作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最新趋势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据我观察,“全球史”概念在中国并不是很流行,但是,我们有必要把它与“世界史”区别开。全球史讲述的是关联和远距离影响的历史,而非民族国家与各大文明的兴衰史,更不是关于霸权和列强的历史。我个人觉得,全球史比世界史更有趣。但是在当今的全球史研究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局部“去全球化”的时代里。
目前的一个新趋势是,人们开始注重研究与信息沟通、思想交流相关的全球史。在这方面,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些理念是从中国或亚洲传播到欧洲的。而迄今为止,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从西方到东方的(思想)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