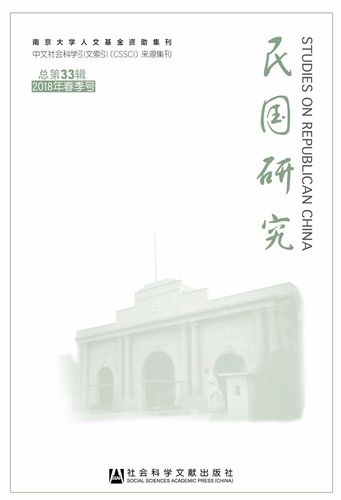王萌 | 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医事卫生调查
作者:王萌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8-07-12
编者按:
日本对沦陷后南京开展的医事卫生调查,由日军军医与日本医疗组织同仁会两方来执行。日军军医的调查建立于被调查者的恐惧与痛苦之上,而为日本战地医学服务。同仁会的调查则包裹医疗“宣抚”的外衣,为日本对南京的殖民统治服务。本文出自《民国研究》第33辑。作者王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日本对沦陷时期南京的统治具有双重面相。一方面,作为傀儡政权的首都,南京在日本的统治下具有展示“中日亲善”的“宣抚”效应;另一方面,基于武力杀伐维系的这一统治,又极具残暴性。以往学界关于南京沦陷史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日本曾有计划地对沦陷后的南京开展过各种医事卫生调查,乃至其背后日本军政当局对被统治者身体的关注,以往学界却鲜有深入的探究。究竟是哪些组织或个人在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又为何,基本史实尚晦暗不明。除利用日本军政当局保留的各种档案资料之外,笔者希望对战时日军军医及日本同仁会医师发表的关于南京医事卫生的调查报告进行史学意义上的解读,考察这些调查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南京民众的健康状况。此外,笔者还希望进一步考察调查者的观感乃至其调查的目的,探讨他们在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统治中扮演的角色,为南京沦陷史研究提供某种有意义的新视角。
一 沦陷后调查工作的启动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对南京地区的医事卫生情报的收集,主要利用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的各种成果。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军部在其编制的《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中,特别强调“上海及南京除文化中心地区之外,因卫生意识薄弱、水质不良、厕所不备、卫生教育落后、医疗设施缺乏等各种原因而传染病流行”,提醒官兵注意“罹患最多且四时不绝的是肠伤寒、赤痢等消化系统传染病,其次为痘疮,霍乱、鼠疫不过为一时流行之疫,长江赤痢、疟疾、急性局部皮肤浮肿及登革热则历来是长江沿岸的风土病”。这份编制于抗战爆发之后,详细记载了南京一带卫生状况的《概说》,实际上是抗战之前日本军部长期收集当地卫生情报的产物。但是,对于当时日本医界而言,由于战前日本从事医事卫生调查的“文化机构”大多设置于伪满与华北,对于华中卫生状况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
南京沦陷后不久,日本军部得以直接在当地开展医事卫生调查。其中可确知的一项是,军医池田苗夫于1937年12月23~25日对南京城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87师、第156师及教导队伤兵191名及普通民众45名进行的血型调查。池田发现,中方被检者的血型以O型血最多,A型最少,这与日本人的血型情况正好相反。池田的调查报告发表于1943年9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第1卷第3号别册,此时他已调至关东军731部队秘密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研究。从报告的细节中可知,池田于深冬的南京在室温保持摄氏18~20度的环境下对被检者集体采血,并大量使用陆军标准式干燥血清,表明了日军为这次血型调查做了充分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如何用正常人的血液为战地负伤兵员进行替代性输血,历来是日本军部关心的研究课题。应该说,池田的调查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的研究兴趣,也是为了满足日军战地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
日军的调查大多隐秘进行,而公开的调查则由同仁会来执行。同仁会是近代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组织,其创办之初的宗旨在于“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普及医学、药学之技术,以促进彼我人民之健康、救济其之病苦”。然而在全面抗战时期,同仁会受日本军政当局指令,派遣多支诊疗班、防疫班至中国沦陷区内开展医疗“宣抚”与防疫工作,意图于沦陷区内建立以日本医学为主导的卫生体系。1938年3月,同仁会专务理事田边文四郎要求被派遣来华的日本医师在开展卫生工作的同时,也要积极调查当地的医事卫生情况,他声称:
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医事卫生之诸法规虽陆续颁布,但多止步于公布阶段。甚而与现实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传染病卫生规则》,也完全不得励行。政府虽发表大量卫生统计,但多不可信。由此该方面的调查研究极具重大意义,实有努力之价值。
对于派往南京等地的诊疗班,田边还强调:
我诊疗班员于当地逗留相当期间,且与大众密切接触,若合力开展调查研究,将不同于匆匆而过之旅行者,即使范围狭小不过为一局部地区,也确信必会获得精确之结果。此为我在华职员明确之使命,亦为吾之一大抱负。
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于1938年4月16日抵达南京,在日军的协助下5月初于中华路下江考棚原南京市立医院开办同仁会南京医院,对当地民众施行医疗“宣抚”。该班11名医师中,包括班长冈崎祗容等7名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其余4名分别为北海道帝国大学医学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金泽医科大学、慈惠会医科大学的毕业生。1938年3月同仁会又于上海设立华中防疫总部,下设南京分部,作为分部部长的台湾总督府技师小林义雄,亦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不久,这些拥有一流医学教育背景的日本医师按照同仁会的指令与日本军政当局的要求,以南京及邻近地区的民众为对象,开始各种医事卫生调查。
二 调查报告所见南京民众的健康问题
同仁会医师对沦陷后南京的医事卫生调查,自1938年5月启动,一直延续至日本战败。
从他们发表的大量调查报告中,不仅可见其调查的内容与旨趣,也暴露了沦陷时期南京民众在健康上的诸多问题。
1938年5~8月,是以班长冈崎祗容为首的同仁会南京诊疗班开展医疗“宣抚”工作的高峰时期。与之同时,医师们对南京市民疾病状况的调查亦很积极,“各科医师燃烧着知识欲,成为一晚上轮流使用石油灯式孵蛋器来确定细菌种类的热心工作者”、“班员无论多繁忙,都不忘作为医者的身份而努力研究”。作为这一期间调查的最主要成果——《南京市民的疾病观》,一经发表即受日本军政当局的关注与嘉赞。
然而,这份报告所见南京民众的健康状况可谓十分恶劣。日本医师们发现,“外科上可见相当多数的创伤,有的放置了六个月,甚至一年以上”,“1837名眼疾患者中罹患沙眼者达1805例”,“内科中梅毒性疾患极多”,“甲状腺肿瘤患者屡见不鲜”。面对大批罹患疟疾与长江赤痢等风土病的市民,日本医师为之兴奋不已,“扬子江畔的南京自古就有疟疾与长江赤痢是当地特有的疾病之说。我等将对之充满兴趣地加以检查,此乃深值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对381名南京市民进行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的检测后,发现被感染者175人,携带率达45.9%,其中蛔虫卵携带者153人,携带率达40.16%。民众携带虫卵率之高,引起了日本医师的兴趣,“今后对此项的调查不得松懈,且要从各方面观察南京市民肠内寄生虫的分布状况,进一步研究与日本人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中国人的被感染情况”。
调查报告《南京市民的疾病观》不仅反映战时南京市民所受的创伤,而且从侧面揭露了大屠杀期间及其后南京治安极度恶化的真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例如,报告中所提到的强盗趁火打劫,用火烧勒索钱财,造成难民严重烧伤的案例,亦为《拉贝日记》等文献所证实。
沦陷初由日军军医对“特殊妇女”、日本艺妓、酌妇实施的检梅工作,在日军南京特务机关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协调下,自1938年6月1日起交由同仁会南京诊疗班来执行。由于事关日军的性安全,医师们对“特殊妇女”罹患性病情况的调查极为重视。从医师杉江善夫的调查报告中可见,1938年末南京城内日军兵站直接控制以外的慰安所有19家,其中仅有6家受到督办市政公署公认。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受日军宪兵队委托,经南京诊疗班诊治的私娼342名中淋病检测阳性率为33.3%、梅毒检测阳性率高达45.7%,当时“特殊妇女”(尤其是非登记的)罹患性病比率之高,可见一斑。
另一项受到同仁会医师重视的课题,是对南京地区小学生的体质调查。1938年8月同仁会南京诊疗班在南京特务机关及伪督办市政公署的协助下,对南京18所市立小学3700名儿童进行了体质调查。结果显示,南京市内小学生男性与女性之比约为3 ∶1,“虽然并非实行义务教育,但当地对女子教育不太重视亦可窥见”;被测儿童的体重与日本儿童的相差不大,身高则略高,相较日本儿童发育状况明显不良,无论男女都有发育上的障碍;南京儿童的各种肠寄生虫卵总持有率达78.1%,其中蛔虫卵持有率达77.29%。另在抽查的儿童2262人中,有996人(44%)患有沙眼,罹患率远高于日本国内的儿童。战时南京小学生的体质极为虚弱,“因战祸而导致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女入学减少,且将来彼等还将因战祸的持续生活状态更为低下,此应特别注意之问题”。
同仁会华中防疫部南京支部,是同仁会在南京开展医事卫生调查的另一支部队。1939年1月,该支部在当地南京诊疗班、日军的配合下,对南京地区疫病流行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共获取病原样本达31308件。1939年4月,日军华中派遣军成立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荣1644部队),以原南京中央医院为工作本部。其核心部门分为四个课:第一课负责病理研究与特殊作业(从事秘密人体实验);第二课负责传染病的预防;第三课负责病原菌的检索与研究,以及预防疫苗的生产;第四课负责野战给水与检水工作。与南京支部关系密切的第三课,直接指导同仁会医师的调查工作。1939年5月,为了配合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防疫研究与对细菌武器的研制,南京支部改称南京防疫处,下设调查部,负责对南京市卫生行政制度、民情风俗、卫生状况、传染病流行、中西医诊疗、风土气候、市民生活方式等的广泛调查。汪伪政府成立之后,南京防疫处的经费大部分由汪伪财政部承担,在日人看来,该防疫处已被汪伪视作“御用机构”。南京防疫处因“‘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第一线的防疫机构若无中国方面行政机关的命令权,就无法对民众展开充分的防疫对策”,故同仁会于1943年9月将之移交汪伪政府,并改名为南京市立卫生试验所。南京防疫处全体日本医师为试验所吸收,日本医师的调查业务一直维持至日本战败。
1939~1941年,在同仁会医师看来,可谓“各处各班进行日常业务性研究、或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最黄金时期”。自1939年12月起,同仁会南京诊疗班每月都会举办班内研究会,“平素调查乃至研究的事项皆可与会上发表,此于多层意义而言,皆有不少裨益”。
南京诊疗班与南京防疫处于此平台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举其要者如下。
医师真忠勤对6244名中国患者、576名日本患者进行了所患疾病种类的调查,发现中国人患结核、疟疾者远多于患消化器官疾病者,而日本人则更多罹患肠炎、脚气、胃炎之类的疾病,这一现象体现了中日国民在疾病罹患率上存在明显差异。此外,他还发现南京市民结核感染中6~9岁儿童的阳性率达41.3%,而警察学校的学员更高达90%以上,反映了结核在南京市民中广泛流行。
疟疾是民众皆知的恶疾,民间谈疟色变。同仁会医师对南京地区疟疾流行情况之调查,下过很大功夫。“为迎接光辉之二千六百年之新纪元(即1940年),当此大东亚建设迈出巨步之际,作为后方第一产业建设后备力量之少年国民在大陆的健康问题,一日不可等闲视之”,1939年同仁会医师对南京及其附近主要城市中国疟疾患者及携带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其中南京地区被检人数为1380人,发现患者149人,罹患率10.8%,“由此可见当地疟疾患者之多数。且大多数患者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治疗”。与中国人较高的罹患率相比,医师细井四郎在对南京市内3所日本人小学502名小学生的检查中发现,日人儿童疟疾原虫携带阳性率仅为2.7%,反映了一城之内两国民众在健康状况上的巨大差距。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医师土屋毅,曾于印度从事医疗工作。自1941年4月担任同仁会南京诊疗班班长后,即于班内大力推行基础医学研究。土屋毅曾对南京1244名中日小学生开展天花免疫力的调查,发现两国儿童在该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尽管如此,土屋认为“南京仍有进一步普及种痘之必要,尤其是对年幼者的彻底普及是极为必要的”。
同仁会诊疗班还对南京市内青年男女对阑尾炎的了解程度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南京军官学校、教导学校、男女模范中学、教员养成所、警官学校、市立中学等学生约2000名,医师通过此项调查获取南京市民的阑尾炎罹患率,并以之与日本人的情况相比较。
医师杉江善夫则比较了南京地区1500名中国妇女与242名日本妇女月经、婚姻、分娩的情况,发现南京气候风土对于日本青年女性的健康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他得出日本青年女性适宜长居南京的结论。
沦陷后期日本医师的卫生调查,还有与汪伪合作的特点。汪伪统治时期,江浙民间清毒运动高涨。有鉴于此,1942年3月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以救治慢性毒品中毒者为名义开设戒烟科,主任是东京帝国大学物疗内科毕业的今堀肇,在治疗方法上该科与“国立中央医院”戒烟科持相同的戒烟法,因“带有社会事业之性质,诊疗班不顾亏损而将该科延续至最后”。今堀肇通过对南京鸦片吸食者的调查发现,1943年时南京登记吸食者为1728名,官方认可的吸烟所为339家,这两个数字较3年前汪伪政府成立时的数据有大幅增长,从侧面反映了汪伪统治后期烟毒泛滥的实相。
三 医师的观感与调查的目的
1938年4月,当同仁会南京诊疗班班长冈崎祗容踏上南京的街头时,他仍能感受到大屠杀后南京城内凄冷的气氛,“即使听说有四十万人口,然而实际行走其间,就会寂寥地感叹,真是如此乎?”从这座城市的一些细节中,冈崎判断着沦陷后南京的卫生状况,“南京作为文化都市,当然还缺乏诸多必要的设施。例如,尚没有最重要的垃圾焚烧场。也没有尸体焚烧场,这或与中国人独特的信仰有关。取自于长江的自来水浑浊而恶质,询之专家,乃知为过滤装置极不完善的缘故。此虽为极端之例,但大体上可知南京卫生设备、医疗机构的轮廓。因此次事变,现今南京市容的大体状况,恰似关东大地震一个月后东京的样子”。
随着调查的深入展开,冈崎很快就发现战后南京民众恶劣的生活环境与疾病流行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调查对象的难民家徒四壁,房屋采光极差,天井很低,地面裸露,屋内仅放一张竹床,上铺竹席而卧,“这就是导致长江风湿症所居住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当然会发生风湿。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南京人将这种风湿称为长江赤痢,多伴随腹泻而发生,这应该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问题”。
日本医师通过观察同仁会南京医院的患者,目睹了南京市民饱受战争创伤的真相。他们看到外科患者中受枪伤、刀伤者甚多,不得不承认民众的苦难不过方为开始,“战争的结束为时尚早”。而中国妇女罹患性病比率甚高,“以往作为调查对象的日本妇女,几乎都是艺妓、酌妇与从事接客的特殊妇女,则可想象确易患病。然而中国妇女的性病分布情况,这着实令人寒心……中国妇女罹患梅毒、淋病之多,正如古语所云‘战争乃性病传播的媒介’,应视之与本次事变密切相关”。同仁会南京医院院长高天成还发现不少儿童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水癌”(即重度口腔溃疡)。所谓“水癌”,即幼儿因营养不良,以口腔为中心开始出现急剧扩张黑斑,不久出现腐烂性感染症,在高看来,“这样的症例自1937年12月南京战后一年多间仅于同仁会诊疗班中所见,此皆因战争之悲惨影响,实令人痛心”。
令医师懊丧的是,战时环境下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其可靠性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在对中国“特殊妇女”性病感染情况的调查中,医师杉江善夫就抱怨因调查对象的流动性,根本无法实施对全员的检查,他认为“现行的检梅工作不过徒具形式,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在医师细井四郎看来,对小学生携带疟疾原虫情况的调查,一般需一周内采血五次方可确定结果,然而现实中检查匆匆而过,根本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细井担忧:“值此新政权临近诞生之际,肩负未来日本命运的小国民的保健问题乃当下之急务。未来我们还计划要对中国小学儿童进行同样的检查,伊始还将会产生中日合作上的问题。”
通过调查,日本医师对于中国人卫生观念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调查之初,他们大多认为中国一般民众因“特有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对疾病缺乏知识,然而不久发现,19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于民间不断推广卫生知识,随着夏令卫生运动等国民卫生工作的开展,相当多的南京市民对于沙眼等疾病已有预防的意识,关于预防疟疾等恶疾的知识在民间也相当普及。
通过解读日本医师的调查报告,可以发现他们热衷于医事卫生调查的背后,除满足自身研究之兴趣外,另怀目的。首先,他们的调查为日本对南京的大规模移民提供必要的卫生数据,着眼于保障当地侨民与日军的卫生安全。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南京的日本侨民不过150人左右。1938年3月“维新政府”、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日本于南京设置各种“指导”机构,大批侨民涌入南京。至1942年4月,除驻屯当地的日军外,日本侨民已达22000余名。侨民滚雪球般的涌入是否存在卫生上的风险,他们的健康如何保障,这些都是同仁会医师关心的所在。正如冈崎祗容所云,他们进行各种调查活动之第一要义,“即要充分考虑未来我国人向中国大陆移民之问题”。
其次,他们的调查协助了日本对南京“宣抚”工作的深入,提升民众对日本医学的好感。在1938年8月对南京小学生的体质调查中,医师就直言这项调查对于“宣抚”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宣抚固然不可少,但对于中小学儿童开展的医疗宣抚,则最具深远的意义。故而我等须先对儿童们的体格进行调查,了解其营养状况,所患疾病种类等,为将来对他们的救治与医学上的预防提供资料”。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宣抚”工作的用意在于把握人心,以此维持日本对南京的长远统治。这从侧面说明,日本医师开展调查的动机,并非来自人道主义的理念,而是来自“医学报国”的意识,本质上是为日本对南京的殖民统治服务。
四 结语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解读,沦陷时期日本在南京开展医事卫生调查的两支队伍——日军军医与以同仁会为代表的日本医师集团,浮出了水面。因一部分关键资料的湮灭,对于前者的调查活动,目前仅能透过军医池田苗夫对被俘军民的血型调查报告,窥知这座隐秘冰山的一角。在池田的调查中,被俘军民不仅是被调查者,也是被实验者,极有可能最终成为被屠戮者。显然,这种建立于被调查者的恐惧与痛苦之上而为日本战地医学服务的调查,其内含的侵略性与反人道主义不言而喻。此后日军军医在南京的调查与研究,以荣1644部队在南京进行的人体实验达到顶峰。
与日本军医的调查不同,同仁会医师的调查则包裹着医疗“宣抚”的外衣。他们的调查本质上是为日本对南京的殖民统治而服务的卫生情报工作。基于此目的而形成的调查报告,反使我们得以窥见沦陷时期南京民众在卫生与健康上的诸多问题。民众的疾苦与创伤,以病症说明、数据统计等形式呈现于同仁会医师的调查报告中,而作为报告的“副产物”,医师对于调查的各种观感亦抒发于其上。他们的观感是复杂的,一些日本医师居高临下,以弘扬日本医学的“文明者”自居,为日本的侵略高唱赞歌;一些医师则不失真情流露,表达出对战争前景的忧虑、对中国受难民众的同情。
外国医师在异国首都毫无阻碍地进行各种医事卫生调查,充分体现了被统治者的屈辱与无力,这是沦陷时期南京不断上演的诸多悲剧之一。事实上,日本医师是日本军政当局对沦陷后南京开展殖民统治的重要协助者,他们对此亦有充分的自我认识。从《周佛海日记》等文献中可知,日本军医与同仁会医师对沦陷时期南京的政治生活有着极深的介入,对傀儡政权高层的健康状况亦了若指掌。深入考察日本医师在南京的各种活动,对于了解沦陷后南京的多元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启示我们,通过医疗社会史的视角或可打开沦陷史研究的新境地。
(点击图片可跳转至购买链接)
《民国研究》(2018年春季号 总第33辑)
朱庆葆 主编
定价:75.00元
2018年5月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2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