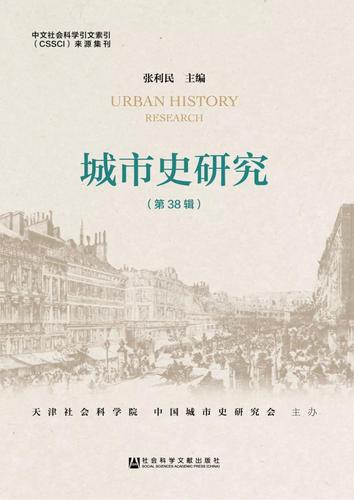路伟东 | 城居与防守:战争状态下民众避祸逃生的一个侧面
作者:路伟东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8-07-03
战争以及战争引发的灾荒、瘟疫,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在短时间内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逐渐增长的人口,因为战争,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年甚至几年之内就损失殆尽。除了造成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战争以及战争引发的灾荒、瘟疫还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极大地改变人口原有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对战后的人口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是中国人口和移民史的重要内容。
同治西北战争是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引发的区域人口变动是人口史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出发,通过复原战时民众在城(行政治所与散布乡间建有围墙并拥有一定防守力量的堡、寨等)内避难与防守的过程,展现战争状态下民众避乱逃生的真实场景,并探讨传统战争中城市成功固守的主要因素。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阐述和分析,可以或多或少地揭示中国历史上传统战争状态下民众避难逃生的模式与人口损失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 同治西北战争与区域人口变动
西北地区是中国回民的传统聚居区,在关中、宁灵及河西等处,回民连片成带集聚,其数尤众。千百年来,回汉两族同村共井,互为乡梓,双方“互讼之案,衅起户婚田土事件”较为普遍。琐碎细故,本人情所不能,官民皆“视为固然者久矣”。然自乾隆中期以来,随着歧视性的司法环境日益加深,双方矛盾往往无法得到合理解决,遂渐诉诸武力。陕省东府(同州)沿渭各州县,械斗之风尤盛。不但次数频繁,而且规模惊人,“睚眦细故,动辄百十成群,持械斗殴”斗杀性命亦不鲜见。而地方团练、螉客匪勇在纠斗之中复以众欺凌,为祸尤烈,常常导致矛盾激化。在这一过程中,太平军、捻军入陕,以及掌教阿訇等宗教因素影响并推动的回民组织化、军事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突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间的不满、焦躁以及歇斯底里的冲动恰恰就是在这种司空见惯、频繁发生的冲突中,在官民的不经意间,日积月累,逐渐凝聚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最终在同治元年以一场惨烈战争的形式释放出来。
从同治元年(1862)初华州圣山砍竹旧史视此事为同治回变之开端。据陕西巡抚瑛棨同治元年五二十六日(丁未)奏称:“华州境内回民购买竹杆,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伤毙回民,当时经人劝散,不意是夜汉民暗赴回村烧毁房屋,于是回民纠众报复,汉民齐团相斗,渭南大荔一带,闻风而起。”到同治十二年(1873)秋肃州回开城请降,西北战事前后持续11年。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战争期间,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口损失。庆阳董志塬延袤数百里,地沃民丰,号“陇东粮仓”,战后却发生粮荒。据不完全统计,仅甘肃一省,战争期间,就至少有18个州县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瘟疫。
以上种种惨相,凡战争所及,几乎每处皆同,“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现有研究表明,仅战争持续的十余年间西北人口损失总数就近两千万,损失比例可能超过总人口的六成。同治西北回民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不但完全打断了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彻底改变了区域人口的民族结构和空间分布,同时,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区域人口迁移。
二 人口规模减小进程中逃难民众往城堡寨的集聚
战争状态下,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但避难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未雨绸缪,及早举家远徙,逃离危险境地,是保全性命的最佳途径。但远徙避祸需要有足够的实力,即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此外,还要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没有足够的实力,既无法远徙,也没有正确的方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整个战争期间,虽然兵火波及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不停地运动之中,奔徙逃命,但其中真正选择及时有效的远离战争区域这一正确途径,并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
对于大多数升斗小民来讲,临战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然事前既无筹谋,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方来则西行,兵从北方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如何逃,往哪逃,逃多久,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从村落空间尺度看,战争初起之时,受波及地区村落尺度的汉民人口迁移几乎就是一种毫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但是,如果从县域空间尺度来看,这种战时逃亡行为又具有较为明显的指向性和规律性。面对频繁的战争逃生情景、庞杂的屠戮焚掠信息,以及对个人和家人未来生命安全不确定性的担忧等,民众往往处于长时间、超负荷的精神高度紧张戒备状态之中。这极易造成心理与生理的调适紊乱,并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应激反应,比如群体性的恐慌、病毒传播式的谣言等。在这种情形下,普通民众的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多的地方似乎有更高的安全感。
于是,那些散布乡间、可达性较好、筑有围墙并且有一定防守力量的乡村堡寨,成为普通民众避难求生的首选之地。除此之外,作为地方行政权力重心的各级行政治城,因系官员衙署所在,一般多有高大围墙和壕沟;即使没有大军屯驻,亦至少有部分士卒把守。这类治城,一般多处水陆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往往也是地方上的经济贸易重心,商贾辐辏,粮财充足。不但可以固守,而且可以久持。因此,相对于大多数的乡村堡寨,治所城市一般拥有更为宽裕的内部空间,可以容纳更多外来人口,是更为理想的避难之所。而战时绝大多数治城最终获得保全的成功范例,也对避难民众有更强的吸引力。战火波及之处的几乎每一座治所城市,都接纳了大量逃难的人口,民众赖以活命者甚众。如省城西安接纳人口就很多,仅北乡和西乡的回民逃入城内者就有千余家。即使是固原硝河城这样一个蕞尔小城,战时避入城者亦高达六百余家。
然人聚之处,亦是财聚之处。人财所聚,乃利之所在,危险亦由此生。另外,堡、寨、治城这类核心聚落又多处水陆要冲,极具战略价值。因此,参战各方的争夺与攻伐相当激烈。从聚落的角度讲,对堡、寨、治城这类核心地方的战守攻防,是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战时民众在城集居避难的场景复原
修城筑堡耗费颇巨,人工财物一切所需,多出自地方。尤其是乡村堡寨,概由本堡民众负担。基于各方面的考虑,一般而言,如无特殊原因和需要,堡、寨、治城的围墙大都修得比较短窄,城墙包围的区域自然也就比较狭促。对于兼具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多重功能的治所城市来讲,衙署、坛庙、书院、仓库及监狱等大量必备的权力机关和公共设施占据了较多空间,城墙以内真正可供普通民众居住的地方并不宽裕。以西安为例,军防和城防几乎占据全城近一半的面积,城市空间非常拥挤。这些有限的空间,首先当然要保证本地居民安全需要。且日用所需一切物资,亦以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为第一要务。而自入清以来,西北地区承平日久,官民均不知未雨绸缪。战争起后,大量民众在短时间内逃难入城,仓促之间,在诸多方面遇到一系列棘手问题。
大量外来人口与原来住户混杂聚居,空间顿显狭促,住房成了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有钱有权者,或可赁房而居,比如鄠县团首顾寿桢举家迁至省城,在湘子庙街租赁房屋居住;郑士范致仕后,入同州府城,亦赁屋而居。但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远没有这么幸运。不管是廊前屋后,还是庙宇寺观,抑或街口渠旁,城内举凡能立足之处,皆为安身之所。如大荔县石槽村村民多在府城的城隍庙附近搭棚暂住。凤翔府城内的情况亦不乐观,“居民扶老携幼,纷纷逃窜至城者,一日数万人……三四日间,满城露宿篷栖,几无空隙地”。
除了居住之处,很多平时习以为常,没多少人关注的事情,比如粪溺、垃圾等污秽废弃之物的处理,在人口骤然增加的情况下也都成了棘手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人畜粪溺,尤其是人粪,向来都是重要的农业肥料,因而,也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在人口聚居的城镇等处,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专门从事相关职业的人群。凤翔府城被围之后,城内“秽积满衢,自夏徂秋,疫疠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守城委钱荫庭、梁倍各家,悉患疫死,有仅存遗孤,有竟绝后者”。这种情况显然并非仅限于同州、凤翔两府,战时治所城市被攻破者虽不多,但遭围困者却不少,城市被围困时间越久,这一问题就越严重。
为保护原来居民的利益,随着战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堡、寨、治城开始关闭城门,不再接纳新的逃难人口。大量避难民众被拒之门外,无处躲藏,往往寄身城墙之下,以求守城兵士可以隔墙庇护。但上无片瓦,下只寸土,日晒雨淋,无所遮蔽。且身处两军之间,多为攻守双方所杀毙误伤,看似身处平安之所,实则立于危墙之下。礼泉县城被围之后,大量逃难民众不得入城者。凄惨之情难以言状。
围城日久,粮食、饮水等一切生活所需,均不敷用。对于城内民众来说,争夺这些基本生活资源实际上就是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而对守城者而言,青壮与物资均为困守所必备。大量难民入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可以吸纳更多有生力量积极防守,但又不得不面对分沾资源的窘境,尤其是大量老弱妇孺基本无益于城守,白白增加消耗。矛盾彷徨之中,需要仔细权衡思量。恰恰就在这轻重缓急之间、本地居民与逃城难民之间,利益互相纠葛,冲突与矛盾亦由此而生。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城市的防守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粮食、水源、饷银与武器:城市防守的重要因素
战争期间,有部分堡、寨、治城凭墙久持固守并终获保全。民间往往把原因归结为神灵庇佑。如同治三年三月,甘肃永寿县甘井寨受到攻击,危急时刻,风沙大作,得以保全。众皆以为“关圣帝君显圣击退也”,乃于战后修关帝庙以答神庥。同治战时,类似关帝威灵感应的传闻与记载,官私文献不绝于书。实际上,所谓关帝显灵、诸神庇护,只不过是惨烈战争状态下,无助民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堡、寨、治城战时能够保全,原因多种多样,每地各有不同,但实皆与鬼神无关。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城坚人众、防守得力之外,还有粮食、饮水、饷银以及武器等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一)粮食与城守
粮食为人每日所必需,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战时众多城堡无力久持,最终沦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粮食给养断绝。治城人口原本就多,战时又涌入大量逃难人口,需求骤增,粮食给养严重缺乏,问题较为突出。比如西安原有人口十余万,战时“又添避难男妇万余人”,同治元年六月初被围后,道里梗塞,米面盐炭一切日用之物皆极度匮乏。守城将官多次派兵到近城河滩草店地方抢运给养,双方于此处攻伐数次。同治三年夏,兰州发生饥荒,“粮价益贵,斗至三四十金无粜者,道殣相望。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携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临潼为西安门户,城小而积少,被围以后,所有给养仅靠骊峰一线转运,攻守双方亦于此处发生激烈争夺。由于城中极度乏食,“难民徒手入城者,数日相继饿死……难民争欲出城挖菜充饥,禁之不可……病饿死者,日计百余人;出城被戕者,日计数十人”。
为解决粮食问题,守城者往往在战争间隙出城抢收粮食以增加粮食。实际上,城中老幼病残等人进城本为逃命,况其中有原本就住城内者,这批人自愿离开城市的可能性不大。真实原因是削减非战斗人员,以节约粮食。陕西按察使张集馨在同治二年的一份奏折中称,“省城难民数万,闻抚巡意欲分散各属以为移民就粟之举,免耗口食,计亦甚善”。所谓难民“分散各属以为移民就粟之举”,实际就是将其逐出城外,令其自生自灭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守城者对粮食的重视程度与绸缪之策,直接影响了最终坚守成功与否。
(二)水源与城守
相对粮食而言,人体对饮用水的需求更加强烈,也更加迫切。战争期间,参战各方围绕水源及饮用水问题,展开过激烈的对抗。不少地方,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围困的人口聚居之处,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比如礼泉县同治二年正月间,逃难民众入城,至五月初,官府开始组织民众在城内掘井,可见此时城内已有缺水之虞。甘肃很多地方高亢,平时饮水就很困难,战时被围,极易陷入缺水困境。陇西分县武阳龙锋堡,被围长达4个月之久,“堡中至煎败皮捣树屑以食,绝水又死者甚众”。部分城堡,甚至因缺水而被攻破。
战争爆发后,被难民众,尤其是老弱妇孺大量投井自杀,但因未及时打捞清理,历经酷暑盛夏,很多水井遭到污染,饮水已成问题。同治元年八月,胜保带兵入关,此时开战仅数月,省城附近的井中皆有积尸,求水已不可得。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戊辰)上谕称,“闻军士前因村镇井水不洁,饮之多生疾病,现更多疯癞软脚之症,回性凶狡,恐其于河水上流置毒,不可不虑,可多凿新井以汲水,或多置解毒之药于水中,并可将病疫之人另为一营,派弁照料,无令仍居大营,以免传染”。官军尚且如此,民众饮水更难保证。战争起后,民众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杀戮、断粮、疾疫等直接造成人口死亡的要素上,对饮用水这种间接导致人口死亡的要素,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实际上,持续性的饮用水缺乏以及饮用水污染与战时瘟疫流行有直接关系,对人口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三)饷银与城守
城市坚守,官弁兵勇所有开支皆出于饷,无饷则难以为继。因此,饷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粮食和饮水。同治战时,有不少堡、寨、治城因饷源充足而最终得免。如高陵县的东里堡,“多富绅,城防诸费并饷兵,需银三十余万,顾皆堡中富绅及邑关一二家任之”。因为饷银充足,雇募了大批壮丁筑堡守城,战时附近民众避居其间者有数万之众,最终皆得保全。
清代陕西商帮资财相当雄厚,尤其是在四川等处经营的陕籍商人,人称“川客家”,不但把持盐茶、皮货、大布以及药材等大宗货物的运销,还控制着四川等省的银钱汇兑、存款、借贷等金融业务。陕商素有乡居、窖藏的传统,“在川贸易者,多将资本运回原籍”,数量相当庞大,“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战争爆发时,陕西乡间有大量窖藏金银。如渭南孝义的严、赵、柳、乔四大家族势力最大,俗称“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泾阳的于、刘、孟、姚四家,亦是大户。俗谚“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王村一撮毛”即指王桥镇的于家。此外,大荔北王阁的景家、西半道的张家,以及富平庄里镇的张家等,也都是累资亿万的巨富。“川客家”的主要聚集区正是同治西北战争的爆发地和斗争的核心区。整个战争期间,陕籍富商巨贾是民间饷项的最主要提供者,且数额巨大。
(四)武器与城守
同治战时,火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功能分类也已经相当清晰。但传统冷兵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装备,城墙的防卫功能也极其突出。对于攻城者来讲,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攻城器械,高大的城墙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尽管此时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拥有足够的火器,尤其是高性能火器,已成为城市攻守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临潼县案例也很经典,该城兵勇仅80人,但拥有比较精良的火炮,铅药亦较充足。每有攻城,城上必开炮轰击。知县谢恩诰称:“是役也,城上所恃者唯铜炮二尊,能及三里外。远见贼骑有首级飞去而身犹乘马者;有白骑忽堕而身已离鞍者;或击之不退,叩祷一次,必能奇中。真神器也!”这两门铜炮,相传系胜保入关时带来的,可能是清军制式装备中的红夷炮。从谢氏的记载推测,该炮有效杀伤距离可达一千数百米,威力相当惊人。守城者对此火炮的神化,甚至崇拜,充分说明了铜炮这类重型火器在城市攻坚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回民中流传“多家娃子,枪子碗大”。“多家娃子”指多隆阿,“枪子碗大”则指其所带的大炮发射的铁子有碗口那么大。寥寥八字,就把回民面对清军火炮时那种惊慌、害怕与恐惧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火器的配备与使用也更普遍。尤其是左宗棠带兵入陕甘之后,经过改良的火器以及更先进的西式枪炮快速取代了冷兵器,成为战守攻伐的主要器械。至此,整个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初期攻守双方武器多以冷兵器为主,高大城墙的作用甚大,双方往往陷入拉锯状态。这是很多堡、寨、治城被重重围困长达数月甚至逾年之久,但仍然可以坚守而未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及至战争后期,参战各方都拥有了较多火器,攻城得力,守城亦坚。无形之中,战争的残酷程度被放大很多。甘肃人口死于战者远多于陕省,与之有一定关系。这是整个西北战争期间,甘肃城池被攻破的数目远多于陕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 结论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就近而不越级是大多数民众避难逃生的首要原则。那些散布乡间、可达性较好、筑有围墙并且有一定防守力量的乡村堡寨,遂成为普通民众避难求生的首选之地。而城墙更加坚固、防守力量更强的治所城市,因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且大多数有获得保全的成功范例,对避难小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战争爆发后,这些相对安全的有限空间,在短时期内涌入了大量的外来避难人口。
外来人口骤然增加,与城内原有人口混杂聚居,住房、粮食、饮水以及公共卫生等一切生存必需均不敷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争夺这些基本生活资源实际上就是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但这些新增人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更多的有生力量,又有利于城市的防守。对守城者而言,青壮人口与相关物资均为守城所必备。矛盾与彷徨间,相当多的堡、寨、治城拒绝接纳逃难人口入城,甚至驱逐部分人口出城。通过复原城居民众的生活场景,可见战争状下民众避难逃生的真实生存状态。同时,也可以展现战争状态下人口迁移最鲜活的一个侧面。
战争初期,攻守各方使用的武器多为冷兵器和传统火器,威力有限,城墙的防卫作用很大。粮食、饮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在城市坚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及至战争中后期,随着经过改良的传统火器以及更先进的西式枪炮的广泛使用,城墙的防卫功能被严重削弱。因此,一旦受到围攻,往往很难久持。堡、寨、治城为人财汇聚之所,亦成利源之所在。且又多处水陆要冲,极具战略价值。参战各方围绕这些核心聚落的战守攻防,是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堡、寨、治城看似坚固,实则为危险汇聚之所,民众避居此间逃命,风险其实极大。实际上,战争期间真正可以成功坚守并最终获保全者数量有限。这是同治年间西北人口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史研究(第38辑)》
张利民 主编
2018年4月出版
定价:8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