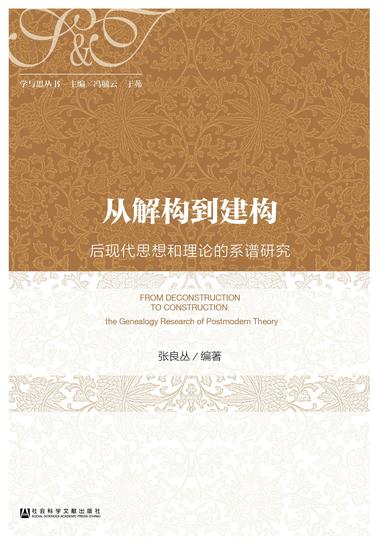从革命的灰烬上弥散开的幻象 | 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批判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7-08-10
伊格尔顿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批评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的前言中,伊格尔顿开门见山地对后现代的一系列词汇及其含义做了描述,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做了区分。他指出:
后现代主义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术语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
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虽然做了如上的区分和概括,但他并不是要把后现代区分为两种现象,而是要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来涵盖两种现象,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文化加以研究,更偏重其思想方面,而不是艺术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穿透当代文化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萌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它所反对和倡导的观念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面对这种文化形式,我们不禁要问应该怎么样看待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观念如何变迁?对此,伊格尔顿也产生了疑问,“这种文化具有多大的支配性或者流行性——它是一直发展下去,还是仅仅表现为当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值得注意。“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予后现代主义以它应该得到的东西,在注意到它的弱点的同时注意到它的力量。”伊格尔顿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是批判的,但在否定后现代主义弱点的基础上也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有其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已经从一种宽泛的社会主义观点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评价;但这当然不应该被看作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相反,它现在也许是比它动荡生涯的任何阶段更加让人讨厌和不切实际的一种观念。……在这样的环境里,放弃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想象,要比欺骗坏得多,默许当代世界这惊人的混乱局面也是如此。那么,我不是说我们手头已经拥有代替后现代主义的完全成熟的东西,而只是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已经试图从一种政治和理论的观点,而不是以某种平庸的常识性反应的风格,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在一个大众对政治普遍失望的时代,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对于正义的设想,因此有必要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辨析,从而建构一个政治合理的社会。因此,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是从政治批评视角进行的。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缘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文化表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科技的发展导致了观念的改变,商业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知识分子的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指向了后现代思想的萌发。
伊格尔顿对此的讨论没有扩展成一系列主题,他把问题聚焦在后现代主义缘起的政治原因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起因在于左派的失败。左派的这个失败不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受人冷淡的失败,而且招致人们明确拒绝的失败。左派的政治学说赖以运作的范式概念似乎已为人们完全忽视,成为一种仅用于收藏观看的古物。在后现代社会中,左派的话语不是被推翻或者被战胜,而是被完全淘汰,成为一种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话语,没有谁会去劳心费力探求它的真实价值。
左派话语的衰败与1968年革命运动的失败有着直接的联系。“经历了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那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一代人。”([英]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2003)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革的时代,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欧美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都是这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场运动中,左派知识分子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随着运动的失败,左派知识分子的声势逐渐跌入了低谷。这些情况恰恰是后现代诞生并且能够流布欧美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失败的左派会如何?伊格尔顿认为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无疑,许多人将或是玩世不恭地或是真诚地转向右派,悔恨他们早年的观点是幼稚的理想主义。其他的人会出于习惯或者怀旧之情坚持信仰,焦急不安地墨守着一种想象的身份,而冒很可能随后患上神经病的危险。最后,还有那样一些信徒,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成为他们信仰的冒牌替代品…… 一小撮左派必胜主义者,无可救药地自信,他们无疑将在最微弱的战斗火花中继续探测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号。在其他人那里,激进的冲动会坚持下去,但是将被迫转向别的地方。人们设想,这样一个时代的支配性假定将是,这个制度本身是不可突破的;大量表面看来并不相关的激进见解都可以看作是出自这一悲观的假定”。革命的希望在这个异常强大的制度下变得不可能了。不过,“抗议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因为这个制度不断地在这种刺激物周围重新凝固起来,使其动弹不得,所以激进的敏感性将相应地分化——一方面是脆弱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对无尽的差异、变动和瓦解的愉快憧憬”。人们将这种冲动转向其他地方,试图寻找一些残存的领地,在其中可以享受不完全处于权力“铁蹄”重压下的轻松愉快。承担这一重任的主要候选者将是语言和性。由此,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人们对这两件事物的兴趣急剧膨胀。当然从后现代知识本身来说,福柯等人提出的话语和性也不是纯粹的革命力量,其背后也有权力在操控,因而无端的快感就成为一种病态,对于语言和性的快感也不会持续太久。从混合了冷漠和实用主义的对病态快感的追求中,就产生了新左派的意识形态——自由悲观主义。这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1968年法国革命》
人们继续梦想着存在一种其制度与现有制度不同的社会。虽然自由的梦想并没有被抛弃,但是没人相信这些会实现,他们甚至嘲笑那些相信它能够实现的天真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含混和不确定的祟拜是必然的,因为当制度完全坚不可摧、彻底的政治改造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对精密和确定的知识的需求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艰苦地汲取大量难以消化的经济学理论还有什么价值呢?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承诺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这种‘思想’既是十足的乌托邦,为了瞥见在它之外的某种现在不可想象的状态,它枉费心机地去探索语言的极限,同时它又是对真正的政治僵局的奇妙替换。”
面对此种情况,浪漫的极左派思想家往往持“内在批判”的立场。因为他们确信,在重视开放并以一定方式实践开放的现存制度的逻辑中存在着“内在批判”,这种批判可以逐渐侵蚀现存制度。制度的他性完全是制度本身的产物,而且它们在其中扮演某种合理的中心角色,具有改变现存制度的权力。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制度、彼此冲突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现存制度”为一方,“持不同政见者”为另一方。这些其实都只是形式方面的区分。实际上,那些反对现存制度的人们,通常是身穿多元主义外衣的纯粹一元论者,他们忘记了制度本身就是与它的核心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在这种意义上,他者与现行的制度是共谋的,并不具有革命的意义。
同样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在任何情况下,社会总体性都是一个幻想”。由此,激进主义者为了给自己提供某种安慰,纷纷抛弃了总体性概念。实际上,传统的总体性概念与革命性是相联系的。被压迫的人们全面理解自己的特殊处境,从而与更大的语境联系在一起,进而去改变它,获得自由和幸福。当然,总体性概念最根本的地方在于其实践主体的存在。但是作为总体性概念的实践主体的人己经因被击败、被收编、被粉碎或者被变形而不存在了。所以,人们要在没有任何可能的颠覆手段的条件下保存颠覆的概念,便只好声称制度会颠覆它自己,这样就将怀疑主义和激进主义融合到一起。可见,在一个政治左派失败的时代,总体性力量已经彻底丧失了信誉,甚至还被认为可能对革命具有阻碍作用。
但是,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后现代对总体性的怀疑通常都是完全虚假的。这种怀疑通常只是针对某些种类的总体性,而对其他种类的总体性却热情认可。如监狱、主教、身体、专制主义政治秩序等总体性就是可以接受的,而生产方式、社会变革、教义体系等总体性则被悄悄地加以管制。总体性也不是都可以简约成为某种单一的决定原则的“本质主义”。没有理由假设总体性总是同质的。总体性就是头脑中的一切观点,其不过是一个被假定为唯物主义信念的唯心主义教条。
从政治批评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不寻求总体性正是不正视资本主义代码的表现。“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更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人们可以预料一种新身体学的崛起,在这个学说中,身体现在是首要的理论主角。”也就是说,在一个正规的压迫性政权控制了一切的条件下,生活中的某个领域仍然残存着一定程度的快乐、随意和自由,也即存在着欲望、身体或者无意识的话语,它们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哲学话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严格限定的世界里,语言或者文本性也会成为自由的这种残留领域,人们可以想象这个及时出现的主角扮演者,它以一系列引人注目地独创性的新哲学主题”丰富了我们的理解。身体、语言、文本性成为主导话题,这就是总体性概念失败的必然归宿。
杜尚《下楼梯的裸女》
当然,这些新的话语的出现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它们可以作为政治批评新领域的延伸。“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终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的商品化、生气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关于社会的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它不是强行地把这场政治失败遗忘,就是一直把它作为假想的对手进行攻防练习。”后现代主义并不承认自己是一种失败政治的产物,它仍然具有政治倾向,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指向是徘徊的。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说既是丰富的又是含糊的。它大谈特谈的重要政治问题已经与传统的问题发生了分离,因为它在传统政治问题上遭受了一场有损尊严的失败。这些问题已经消失或者已被解决了吗?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政治实践革命活动中已被证明是难以解决的。这就需要发现新的政治问题。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符号和性,到之后的符号和性开始被模糊和怀疑,最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只剩下性,这种转换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并不是随意的替换而是标新立异。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语言和性都具有政治性,谈论语言和性也就是在解决政治问题。所以,从整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已经把性、性别和族性问题放进了政治日程,替代了更经典的涉及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物质生产方式的激进政治学。后现代主义只是在话语的层面保持了政治的热情。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主体的确具有替代性的功能,但是对传统主题的忽视也导致了很多激进政治分子因政治无知而患上了一种历史健忘症。
而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后现代主义确实是鲜活的存在。“它们不仅提出了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问题,而且出现在有着数百万观众的理论的中心舞台,这些人通常不但被制度本身而且被传统的左派所弃之不顾。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主张不仅表示为一系列新鲜的政治要求,而且表示为这些政治概念的想象性变形。”后现代政治观念的诞生,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它代表了一个更早时期的憔悴、贫血、沉默寡言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政治学的继续深化。在伊格尔顿看来,对于传统政治学的基本观念——阶级、意识形态、历史、总体性、物质生产,以及支持它们的哲学人类学,我们都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经典左翼思想和与它相对立的某些统治性的范畴之间的共谋关系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后现代主义给那些被侮辱、被谩骂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立场,而这已经威胁、动摇了现存制度及其核心的傲慢的自我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政治观念虽然有缺陷,但也有其积极价值和意义。
后现代主义是模糊和两面的。它在短暂的存在历程中生产了涵盖文学艺术全领域的一大批丰富、大胆和令人振奋的作品。它颠覆了确定性观念,评判了某些妄想狂的总体性,撬动了某些压迫性规范,动摇了某些脆弱的基础。同时,它模糊了人们的身份,产出了给人鼓励也使人麻痹的怀疑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在试图从其脚下夺去基础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拆了自己的台。所以,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观念,还需要站在特定的立场加以反思。“这种针对概念上穿紧身衣的反对意见存在问题。首先,很难看出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历史决不是特殊的……再者,上述事例有形式主义的嫌疑:每一种将历史纳入一种特殊模式的企图都和其他任何一种同样有害吗?公民人道主义也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有害吗?这似乎难以置信:人看来需要某种进行辨别的差别精细的根据,但是还不清楚它们来自哪里。也许它们源自这一途径,即从一个形式上的观点召唤出一个道德内容:世界本身只是一出差异与非同一性的无尽戏剧,最残酷地压制所有这一切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是最应该受到指摘的东西。”
推 · 荐 · 阅 · 读
从解构到建构:
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
张良丛 编著
2017年7月
本书在综合考察后现代发展的基本线索、分析各种代表性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以建设性后现代主张的问题意识为基础,秉承建设性后现代“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 、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上,重构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的宗旨,力图从后现代思想理论中,挖掘其创造性的存在物、本体论的平等观、生态主义、有机整体性、过程性、对话、他者圣性等富于建设性的理论话语,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提供正确的新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