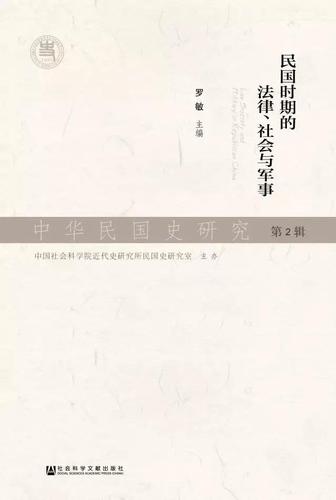李志毓|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1924~1928)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6-11-30
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始于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当时孙中山一方面迫切需要苏俄物质援助,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组织涣散、军人恃权、党员无力,党的主张无力,“姑可张罗于一时,恐日久必穷倒”,“非从下层多做功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改造中国之伟大责任”。因此决定借联俄之机,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实施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军校中负责政治工作的机构,一为党代表,二为政治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继承联俄联共政策,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在军中大力推行军事委员会、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展现出一种务使散漫于中国的武力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党治军的决心。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统一改编国民革命军,设立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党代表和政治训练部作为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机关。在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体系建立初期,党代表在军队中位高权重。按照1926年公布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党代表是军队中党务工作的领导人,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和一切组织工作均受其指导,还要指导所辖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条例规定,党代表和指挥官一样是所属军队的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的权力,当党代表认为指挥官的命令危害国民革命时,应报告上级党代表。但若发现指挥官有明显的变乱或叛党行为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这些规定,几乎赋予了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职位,一直由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担任。黄埔军校创建之初,孙中山曾委任廖仲恺担任军校党代表。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接替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4次会议上,被推荐为各军及各党立军校的党代表。1926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又通过陈公博的提案,改任汪精卫为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同年4月,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称病离职,总党代表一职由汪的亲信陈公博代理。廖、汪、陈三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都是积极联共的左派。 党代表之外,另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机关是政治训练部。它上承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指导,下辖各军、独立师、海军局、航空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参谋团、军需局党代表。第一任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陈公博。1926年6月,北伐筹备时,政治训练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部长邓演达,大量吸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加入其中。在总政治部下辖的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总务科中,担任领导工作的主要是共产党人,例如秘书长恽代英,秘书处长孙文炳,宣传科长朱代杰,曾任秘书处长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总务科长江董琴,先后任宣传科长、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革命军日报》总编、社长潘汉年、杨贤江等。 在总党代表和总政治部之下,各军的军、师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也多为共产党人。例如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该军第四师党代表李六如,第五师党代表方维夏,第六师党代表萧劲光,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罗汉、张善铭、廖乾伍,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兼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第八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彭泽湘等。师政治部下设的宣传科、党务科和各团、营、连级的党代表,也多由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担任。 为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首先,这是共产国际的一种战略设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非常重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当军事指挥官,在国民党军队里不设共产党支部,不发展共产党员,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军队政治工作,改革国民党军队中的军阀制度。 其次,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一方来说,共产国际在国民党中大力推行军事委员会制度和党代表制度,试图形成集体领导和以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一举解决党内新军阀的问题,这正与他的期待不谋而合。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借助苏联顾问的力量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以一介文人而能在军队中施加影响,极大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汪精卫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如何以党治军、限制中国武力的恶性发展,是汪精卫长期思考的问题。 1927年4月,汪精卫回国之后,试图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他感于国民党各军的军事机关和特别党部之间隶属关系和指导权划分不清,与陈公博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请批示“军委会所属各军及军事机关特别党部总纲”。提出:第一,特别党部隶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特别党部应受党代表之指挥及政治训练部之指导;第三,特别党部之组织由政治训练部秉承中央之命令,指派党代表或政治工作人员组织之;第四,特别党部之党务应呈报政治训练部转呈中央党部审核之;第五,政治训练部秉承中央之意旨,办理特别党部一切指导计划等工作,并传达中央党部之命令于特别党部。总纲规划了军事机关中一个自上而下垂直领导的党务系统,事实上是要将军队中的党部和政治训练部从军事指挥系统中独立出来,直接隶属上级党组织,这再次强调了政治对军事的监督和指导地位。 国民党北伐之前,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内训练,即对政治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对基层官兵的教育。1925年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开设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由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等7人组织理事会。学员有来自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50名,湖南省党部选送的100名,及全国各地投奔广东政权的知识青年,共382人。1926年春正式开学。主要课程有张太雷讲授《世界经济状况》,邓中夏讲授“职工运动”,郭沫若讲授“革命文学”、蒋先云讲授“军事运动”,萧楚女讲授“社会主义”,毛泽东讲授“农民运动”等。北伐出师前,总政治部又将政治讲习班的骨干学员和广东大学部分学生集中起来,开办特别训练班,开设了“反吴之意义与政策”“党务”“政治工作方法”“各省军事政治报告”等4个专题讲座。这个训练班,培训了北伐初期的部分政工人员,训练结束后,部分学员被分派到军队中工作,还有部分学员回到湖南做地方政治工作。 北伐开始之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心,由训练转向了宣传。虽然士兵教育,特别是对新兵和俘虏的教育,仍然是重要工作,但在当时总政治部编辑的各种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手册中都可以看到,作战演讲、唱口号和歌曲、贴传单、与民众召开茶话会游艺会宣传工作,被赋予了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总政治部印行的《战时政治工作人员特别惩戒条例》(14条)中,有5条与宣传工作直接相关,凡“不向民间宣传本党主义者”,“不遵守宣传大纲者”,“每到一地有一日以上之勾留而不开联欢会或其它游艺会宣传会等者”,“不利于时机向士兵夫役及俘虏宣传者”,“军队所过之处不贴标语者”,将“处予以撤差,降级,罚薪,记过等处分并按照党纪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 北伐时期,左派主导下的军队政治部,招收了大批文学青年和年轻的画家、音乐家、摄影家参加军队政治工作。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很多优秀的左翼画家曾在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系统服务过,如黄文农、许幸之、叶浅予、关良、司徒乔、鲁少飞等。鲁少飞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他的《北游漫画》收集了参加北伐一路上所作的39幅速写,书后有画家戎装的照片,题为《二十五岁的我》。著名漫画家黄文农在1927年北伐军进驻上海之后,曾担任过淞沪警察厅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长。1927年出版的《文农讽刺画》,便是他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创作的漫画结集。 著名画家关良,也受到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的邀请,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参加了北伐军。他在回忆录中说:“全股共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些是留学过的大学生,而且大都是些学有专长的人。此中有专搞绘画、电影摄影的,也有搞新闻照相的,有的能歌善舞,有的能编会导,加上我和几位擅于画画的,又喜欢操琴弄弦,真是巧合天成,充分显示出青年人的聪明才智和勇往直前的革命朝气。”著名画家司徒乔是1927年2月经人介绍到武汉鲍罗廷办公室做美术宣传的。他在回忆武汉那段革命时光时说:“好一场大江上的革命之梦!那梦里的死,伤,凶,肉,和伪善的憧憬,和那犹羊无牧,所谓革命的群众,我是永远不会在我的色板上忘遗的啊。” 尽管政治宣传工作被赋予重要地位,其成效却不能一概而论。关良曾在回忆录中说,艺术股的同志们不顾长途行军疲劳,每到一地,就忙于四处刷标语、画漫画、搭戏台。“讲演、相声、快板、花鼓等短小节目,把各个宣传阵地搞得热气沸腾。战士们得以在战斗的间隙中休整、调剂,振奋精神,提高士气,老百姓们也得以了解到战况,形势很好。”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朱其华的回忆录,却显示出宣传对于战争胜利的意义不可高估。朱其华说:“在广州出发时,我们本来领到了几千元的临时宣传费,所以也印了不少的书报、画片,小册子,传单,宣传大纲;而且准备了许多宣传计划。可是实际上,自从出发以来,除了每到一个地方分送些宣传品,留声机般的作些讲演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而我们那种讲演,听的人未必就能懂。”自南安出发以后,对于宣传工作更是随随便便,很多人倒是在船上热心地赌博起来。 国民党早期的军队政工人员,多是些热心政治而未经军事训练的青年学生,任用过程既随意又匆忙,就缺乏必要的训练和考验。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原主任陈公博曾说,政训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最初训练了120名政工人员,开学不到两个星期,就全数调赴东征前线。后来党内鉴于政工人员不足,将黄埔军校改为政治军事学校,特设政治班。可是不到毕业,又调赴北伐前线。自北伐开始后,政训工作范围愈广,经过训练的人员不够,就调拨军校未毕业的学生,军校未毕业的学生不够,就征召普通学校的学生。到了长江流域之后,甚至变成似乎是谁穿上军服,谁就可以做军队政治工作。 这些受过中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远离家族桎梏、礼教束缚,又投身于打倒一切压迫之革命事业,思想解放、行为浪漫,更时常鼓吹恋爱自由。朱其华在回忆录中曾讲述了一位同时与三位男性恋爱的“女秘书”的故事,并认为“这决不是党国之耻,而是党国之光!我们应该自豪,我们有了比潘金莲潘巧云辈更伟大的英雄,这是表示我们至少已经相当的战胜了封建意识”。他还说,没有一个机关比总政治部更腐败、更堕落的,“他们个个都打着雪亮的皮绑腿……他们把整篓整包的宣传品,在田野间乱丢,这样,他们的工作报告上可以写‘散传单几十万,散画报几十万,贴标语几十万’……当我们在前方作战的时候,总政治部的同志躲在后方,在后方的民众面前做他的老爷。但是,当我们把敌人打退以后,总政治部的同志就来前方照相,演说,向我们训词了”。 这样的政治工作人员,与出身破产农民家庭的普通士兵之间,常常产生隔阂;刚刚走出校门,没有多少军事知识和社会阅历,突然被委以重任,又容易引起军事长官的不满。某些政工人员的品行和作风,与军队的风气也格格不入。冯玉祥曾教育自己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当深入兵众中,与士卒共甘苦,切勿效法武汉之政治工作人员坐花车,吃大餐,身备五皮三金,男女拥抱跳舞,致令士卒生忌,宣传失效也。”还有人说,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与军事长官的关系,“不是各军装饰门面的机关,便是军事长官的留声机”,大多数军事长官对待政治工作人员,“不是客客气气的虚与委蛇,便是表示鄙视的心理”。武汉政权解体之前,政治工作已变成了军事的附属品。有人说,政治工作变成了军事的“姨太太”。这种情形,让政工人员深感痛苦,而“减少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牌与喝酒”。朱其华说,他们把武昌所有的菜馆都吃遍了,“政治部拿来的饷,几乎全都化在打牌与菜馆里了”。“所有的朋友几乎全和我一样”,“我们不约而同的渐渐堕落下去……武汉政府也就是这样的一天天走向坟墓里去!” 国共分裂后,为了跟共产党划清界限,确立国民党左派独立的政治纲领,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开始思考重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在武汉“分共”后出版的《中央副刊》上,有文章指出,过去政工人员“多半是书生”,缺乏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对于革命理论和政治知识又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造成种种“浪漫”和“幼稚”的弊端,以后的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严格的军队化和科学化,要做到行动劳动化、生活规律化,绝对依照军队的礼节和纪律行动,切实执行总政治部规定的惩戒和考勤条例,接受军事训练,对于总理的主义和本党的宣言决议训令等,要有切实的认识,对于工作对象、工作方法、社会情况等,要有真确的考察。除此之外,还要切实深入群众,深入士兵当中,不应离开了群众,只和机关办事人员“作无谓的周旋”。 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分别下野,1927年9月,与汪亲近的张发奎、黄琪翔部,借口“清剿”南昌起义的贺叶余部,率军自江西南下,控制了广东,喊出“拥护汪精卫”“粤人治粤”“改造新广东”的口号,并电邀汪精卫来粤。10月29日,汪精卫偕陈公博到达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提出保护农工、惩治贪污和整理各级党部的计划,并开始推动军队政治工作。1927年11月8日,在广东省政府洋花厅举行的各级政治部联席会议上,陈公博以主席的身份,回顾了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和目前面临的困境。 在会议上,陈公博认为,政治工作至今仍不能在军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才缺乏和国民党培养政治工作人才的机制。但从会议记录来看,人才缺乏的问题并未被充分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统一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宣传案》《各级政治部应统一编制名称及确定经费案》及《提高政治工作人员地位案》等一系列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案,但均停留在具体工作的层面上,对于最根本的“人才缺乏”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对策。 1927年12月,共产党趁广州时局动荡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汪派在广东重组政府的步骤被打乱,国民党内随即对汪派展开凌厉声讨,指控他们“甘受第三国际指挥……唆使张黄窃据百粤、勾结共党、焚劫广州……”汪的政治主张和个人声望都受到严重打击,再度流亡法国。1928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四个月后,通电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幕,组成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和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等“左派”均被限制出席。1929年的国民党三大又议决:“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的党籍,开除顾孟馀党籍三年,汪精卫由大会给以书面警告处分。以汪为首的粤方委员被正式排除出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潜居法国的汪精卫,并未忘怀国内的时局发展。面对北伐结束后,事实上武人割据、党权破碎的局面,汪苦心积虑地思考着怎样使国民党从军人控制中解脱出来,并进一步以政治力量控制中国武力的问题。 使武力为民众的武力,摆脱军阀的控制,这是孙中山生前念兹在兹,汪精卫也反复重申的主张。怎样实现这一诉求,有上下两层工作要做。第一,是用党的纪律约束军事将领,使将官跟着“党”走;第二,是使下层的士兵变成革命者,即军队本身由革命民众组成。汪认为,欧洲的革命,是民众先有了武装,然后民众的武装与专制君主的武装相冲突,最后君主的军队逐渐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叛变君主。苏俄红军则是革命成功之后,由革命民众组成军队,因此军队与人民趋于一致。而中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革命的军队不是革命的民众里出来”。换句话说,民众本身是落后的。 汪精卫说,中国的革命,都是由一些先进的革命党人发动,由革命党人一边唤起民众,一边组织军队。因此军队的来源不外三种:一是革命党人利用社会上的武力,如绿林、会党,使之变为革命的军队。二是军队的将官是革命党人,得到机会,统率所部起来革命。在国共合作之后,开始有了第三种方式,“便是由党立的陆军学校里,养成将官以组织军队”。但这种组织军队的方式,汪精卫认为,似乎可以假定所有将官都是革命者,但所有士兵仍然不一定是革命者,“因为所有士兵都是招募得来的”。因此,“将官革命,士兵也就革命,将官不革命,士兵也就不革命,士兵一定跟着将官走,而将官不必一定跟着党走”。总之,仍然不能摆脱兵为将有的传统,建立“党”对于军队的统一领导。使军人从认同私人将领,转变为认同于“党”。从汪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从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着手改造军队,是根本的途径,但是速度“太慢”。 同年6月,汪又在给王懋功的信中说:“若要打倒军阈,先要以党治军。所谓党者,舍总理外,决无可以个人之意思,为党之意思。故至少限度,须用合议制,在此合议制中,武人、文人皆不当有所分别。武人之力,须在合议制外发动……在合议制中,武人不能有丝毫挟持武力之行动,如其有之,即为叛逆,立当锄而去之。”可见,经过几番挣扎,汪精卫最终决定诉诸通过上层制度建设,建立集体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以“党纪”约束军人,达到以党治军的目的,而完全放弃了国民革命时期那种由上到下、利用党代表和政治部约束军人、教育士兵的军队政治工作模式。这表明汪精卫虽然以“左派”自居,但在最关键的——从下层入手改造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问题上,放弃了孙中山的改组精神。这或许也是汪以一介书生,手中既无可靠军队,又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扶持之后,一种无奈的抉择。 国共合作时期是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初创和繁荣时期,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局面,导致国共分裂必然伴随政治工作的由盛转衰。北伐结束后,国民党虽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民国初年以来的政治军阀化趋势则有增无减。各路军事领袖如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等,不仅拥兵自重,相互猜嫌,且借助各地政治分会,掌握着地方政权,形成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收编各省军队,大量扩充,快速壮大。北伐出师时,国民革命军共有陆军8个军、28个师、9个旅、111个团、4个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少量海军、空军,共约15万人。至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收复北平、北伐结束时,全国已有90个军、282个师,共计202万人。这些迅速扩张的军队,未经政治训练,事实上仍是旧式的军阀部队。 1937年3月13日,在距离武汉从“联共”高潮走向“分共”将近十年后的一天,汪精卫又想起了他早年的至友蔡元培,并致书一封说:“数年以来,音讯隔绝。去冬归国以后,始从诸同志处获悉近状,向往之心,与日俱积……铭不自揣愚顽,妄欲揭以党治军之义,与持兵者相抗,颠顿至今,一无所成,而坚执此意,仍不少衰……数年以来,国人属望本党,以为可以拨乱致治之意,已因个人独裁,借口党治,摧残民权,种种事实,使属望者变为失望。长此以往,只有日即沉沦。言念及此,殷忧内集。未知先生何以教之。”蔡元培在回信中说:“先生提以党治军之义,诚为扼要。以今日军队之复杂、军人领袖程度之不齐,同仇则暂合,投骨则纷争,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将如何彻底整理,使一切受党权支配……此关打破,始可以着手于其他问题。”此时,正是日军大举侵华和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久,而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混杂纷争的问题,反而愈演愈烈。汪精卫所追求的“以党治军”体制,在国民党政权中,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本文选自《中华民国史研究》第二辑,作者李志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