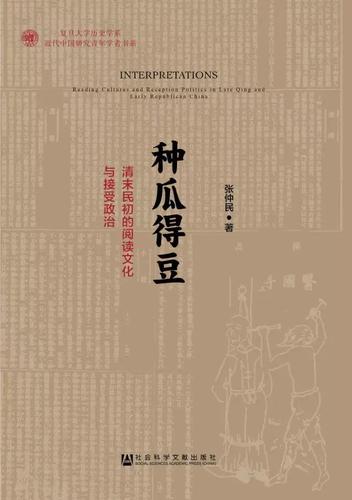清代禁书令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6-11-24
在中国,历代颁布的禁书之令为数甚夥,而清代尤甚。撇开政治层面的禁书不提,清代禁书令中有许多是针对小说、戏剧、唱词等通俗文学的,其查禁这些通俗文学类书籍,往往指以“淫书小说”、“淫辞小说”等名称,以其于风俗人心、社会秩序大大有碍——“诲淫诲盗”而禁之:
一切鄙俚之词……大率不外乎草窃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斗狠者,溺于邪慝,转相慕效,纠伙结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书词所致,世道人心,大有关系。
这里所谓的诲淫诲盗,多是统治者和士绅精英的强加之词,便于为查禁行动寻找合法性。实际上,这些文类虽包含有不少情色、非圣无法成分,比如,许多农民造反便是直接袭用《水浒传》等书中的口号与组织形式,从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到天地会、湖南瑶民起义,都是显著例子。有的甚至连战术、战略亦效法《水浒传》。例如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其埋伏攻袭咸效之”。但亦承载有很多正统社会推崇和宣扬的教化观念,有严肃与正统的一面,情欲、暴力和教化在此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当然,其中的某些文类确实属于露骨的色情之作,内容非常淫秽,尽管自序“十九以劝诫为借口”。
此处姑且不论其中所禁之书是否“诲淫诲盗”和是否当禁,类似禁令的屡次颁布与诸多论述的不断生产,虽可表明朝野间对此问题的关注及警惕,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说明这类禁令与论述的实际效力或许并不大:“功令虽有严禁之条,而奉行者多以为具文。”即或有厉行禁令者,也收效甚微:“思夫淫辞邪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未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止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止于阅者之人之心。”另一方面,自然也表明这类书的普及程度与影响力——“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此种现象绝非区区律法就能禁止,也非道德训诫就能力挽狂澜,特别是在私人刻书风行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时期。
然而,在大厦将倾、新学流行的清末社会,受到新学影响、力主文化改造的启蒙人士——主要是一批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的新知识分子、趋新士绅、开明官员、新式军人等,受到世变之亟的刺激,意识到“今日法固不能不变,变法根本,端在读书”。在他们看来,中国士民久处于专制政治之下,风气闭塞,眼光狭隘,不关心国事,不具备国家思想:“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以为国之强弱,于己之荣辱无关,因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且普遍迷信“怪力乱神”,“文明”程度非常低。
在此情况下,启蒙者开始将大众阅读视为一个关系国家兴亡的政治问题,19世纪第二共和时期,法国改革者和政府也发起了一场改造民众阅读的运动,不许各个地方图书馆收藏有争议作者的作品及一些异端的政治著作,希望能将有害于统治秩序的出版品包括一些文学读物,从大众的阅读品中剔除出去。决心采用启蒙论述来规训老百姓的阅读文化,并借用西方这个象征权威来背书,承续以往正统的禁书论述,凭借新的思想资源及传播媒介,发起一场旨在改造大众阅读、禁止他们阅听“淫辞小说”的文化实践。
在古代中国,信奉“正统知识观”的官方和知识精英制造了大量关于阅读、禁书、禁止“怪力乱神”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不少是针对下层百姓而言的,就是大量禁止他们阅读某些通俗类文学书籍或阅听戏曲,禁止他们迷信“怪力乱神”。其实,民众接受“怪力乱神”与欣赏“淫辞小说”,未必一定走上同当权者和主流意识形态、礼仪纲常相对抗之路,经常不过是一种像游嘉年华一样的游乐观赏行为而已。如时人之言:“社会不能无游戏之事,以舒适其性情,故愚夫愚妇之入庙烧香,非必尽迷信神佛也。春秋暇日以从事游观,亦人情之所不可无也。”远不如称之为“娱乐”和英雄崇拜准确。恰如之后有学者所言:
中国风俗之祀,与其谓之迷信,毋宁谓之娱乐。如清明端午活动……又中国祀神之俗,与其谓之迷信,毋宁谓之崇拜英雄,如关公庙、岳王庙等,遍于国中,其人则中国先民,其事则垂诸青史,并非三头六臂、飞行绝迹之怪物也。
然而,在部分官方及正统人士那往往有妨碍社会稳定的认知与担心,发布和推行禁令自然是应有之义,再饰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其目的无非还是端正风俗人心、翼教卫道,维护专制王权的统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控制,预防这些文类惑世诬民,出现不乐见的后果。这些论述尽管大多是由官方或知识精英制造,不足为我们完全采信,但是,历史上的下层民众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自己生活、阅读、思想和信仰的记述——他们直接提供的证据太少。我们转换视角,由这些官方论述出发,反其道而行,或亦能对前现代中国下层社会流行的阅读文化及通俗文本有些许认识和体会。
实际上,那些官方和知识精英屡禁不止的读物,因其浅显、通俗、富于趣味和故事性,且贴合一般民众的生活及期望,往往是庶民百姓乐意阅听的;而他们所推崇的教化、训令,因其繁杂、艰涩,且常常带有强迫性质,往往让老百姓心存芥蒂、漠不关心。中国历史上下层民众的阅读习惯以及思想的生成固然同官方和知识精英的教化有关,但由于知识水平比较低,绝大多数人甚至不识字,日常的阅读和娱乐兴趣依然是稗官野史、听大书、看戏剧等。
这些被视为“淫辞小说”的文类以生动、形象、扣人心弦的叙述和寓意宏大、褒贬明确、引人浮想联翩的修辞,展现人们对于人情世故、天道自然、善恶祸福、社会秩序、忠孝节义、礼教纲常的认知(包括服从、暌隔或反抗),实际昭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精神生活、期望及其如何面对、看待他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尽管这些文类存在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不太协调的成分,但它们本身亦承载着正统教化与道德训诫:“内地各省城乡弹唱稗官野史者流,如《三国志》、《说唐》、《说岳》之类,每逢鼓板登场,听者塞座,验其实效,虽事隔久远,间涉荒唐,然无论妇孺皆知某也忠、某也奸,了如指掌。此习惯之可证者。”
上述的种种情况,均表明“淫辞小说”类读物受欢迎的程度。故有人总结道:“下流社会中,虽不能读经史等书,未有不能读小说者;即有不读小说,未有不知小说中著名之故事者。”进而言之,这些“淫辞小说”类读物并非只有引车卖浆者流、妇女或孩童喜欢阅读,即或是士大夫、达官贵人也分享这些文类和此种阅读文化传统,阶级或财富并不构成阻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貌似大相径庭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其相通、相融处通过阅读相同的“淫辞小说”亦表现出来。
约言之,一般大众热衷于接受和阅读的毋宁是那些“怪力乱神”、“淫辞小说”,而非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教条,长期在这些通俗文类的耳濡目染下,一般人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
在19世纪末以前,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在地的士大夫,他们都主张禁止老百姓读这些“淫辞小说”,个别有远见之人如钱湘,也认识到要找出如《荡寇志》之类的替代读物,才能达到不仅禁售者,亦并使阅者不取阅“诲淫诲盗”这类书的目的——“兹则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严其禁耳。”
19世纪末之后,禁“诲淫诲盗”这类书的论述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乃至于士人阶层,依旧有不少表达,出发点也与之前相同。甚至是当时的新学才子梁启超,亦有相同认知:“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在稍早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梁亦曾说中国古代文人之文“诲淫诲盗,不出两端。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不同的是,在梁启超发表这类言论的时代,特别是由于庚子年义和团事件,许多士人迷信“怪力乱神”,认为洋人船坚炮利不足畏,拳民皆可以术破之,其结果众所周知。
不过,禁书乃老生常谈,大家早已领教多次、司空见惯。且从以往查禁效果来说,收效不大,经常会适得其反,在清末新式传播媒体大量出现的情况下,还会招致舆论抨击,倒等于给被禁的阅读品做了广告,愈禁愈增加其分量和销量。禁止阅读显然不能正本清源,要想不让大众阅读某些书,就必须预备相应的读物代替,否则效果不会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生产出合适的替代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才是“不禁之禁”之道。“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没有读者的阅读,新的文类生产再多又有何用?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
文字摘自
种瓜得豆
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
张仲民 著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