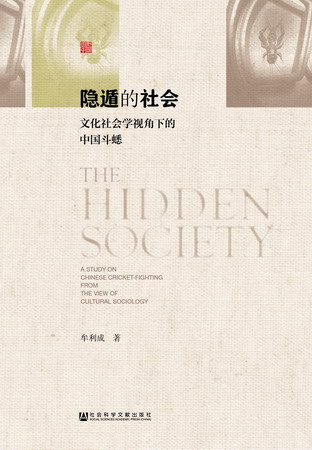隐遁社会 | 斗蟋、熟人社会与“关系”互惠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8-01-31
斗蟋群体可谓中国社会中隐遁的一面,鲜有人关注研究。然而这个地下小群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深入其中并非易事,最重要的引介在于友谊与“人缘”。
同时,虽然斗蟋者都有着金钱利益的追求,但究其根本,促使其乐在其中的动因并非金钱驱动力,“交往”本身成为了目的。这也不难解释,在“现实”社会中身份地位悬殊的人,在斗蟋群体中反而能够结为十余年的稳定伙伴。
情谊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谊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形式。给人们一个场域、一个引线人,人们就会像蜘蛛般“穿针引线”,以自我为中心,在不同的独立个体之间建立起如丝线般连的关系。当然这种丝线对对方的钩挂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对你所抛出的丝线的回应强度。人们之所以回应,其原因很多,有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有的是出于对自我力量加强的考虑,有的是处于安全的预期,比较特殊的是出于一种情感——亲情、友谊和“缘分”。
在斗蟋这个隐遁的社会中,人们以虫会友。虫(斗蟋)是这一社会中人们建立关系的独特介质,在这种独特的介质上面,表面涉及最多的好像是市场经济所涉及的金钱,但是金钱一直没有成为这个社会中如市场经济中那样几乎万能的媒介。斗蟋者来自五湖四海,互不相识,但是为了一种嬉戏,他们相聚,在相聚的过程中他们相互了解、结识,最后相互有选择地成为亲密或一般的朋友——其中当然不乏因为脾性不投而反目的。但总的来说,斗蟋这个隐遁的社会是一个由“朋友”构成的熟人社会。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样式的。在这个社会中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同的是前者的一个主要的引介是亲情、地缘和血缘,而后者的最重要的引介是友谊和“人缘”。
要了解斗蟋这一隐遁社会空间中的人际关系情况,必须和其中的人结识,而要结识则必须经由一条如科林斯所描述的“互动仪式链”。在科林斯那里,整个社会被看作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由此人们从一种际遇流动到另外一种际遇,而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个网络想让你看到的部分。
2008年,当笔者还不懂蟋蟀的时候,就靠这一股闯劲参加了当时的全国蟋蟀大赛。当时自己与南通蟋蟀协会的会长只是在开幕宴的时候见了一面,并且除了互视微笑也没说什么,一场比赛完后他突然说要到笔者房间找笔者聊天。结果我们一聊就是一个通宵。笔者主要是充当了一个倾听者。他是南下干部子女,很小的时候父母参加革命,就把他寄养在一个山东农民的家中直到其9岁。这也许是他对笔者这个山东人表现出特别好感和有兴趣的原因吧。
这种彻夜长谈,很快在促织园的小圈子里传开了。很多人都很感兴趣。有的会经不住好奇地问一句:“你们真谈了一个晚上?”在他们看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有什么话需要说一晚上啊?在这个沉默的社会中,它的表面逻辑是行动比言语更重要,但是后来随着笔者对这个隐遁社会接触的增多和深入,笔者发现好像正好相反,这个社会是那样地渴望相互交流和诉说。当崇明岛“促织园”斗蟋的人们对我们的彻夜长谈感到好奇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羡慕和祝福的成分在里面,因为要不是两个人有很多话要说,要不是很投缘,怎么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聊一个通宵?更何况第二天还有比赛。
那次彻夜长谈本身,以及后来人们私下对长谈的善意议论,都让笔者感觉很温暖。它让笔者觉得如果自己只身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也不会觉得孤单。这种忘年交的友谊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厚实。因为距离的遥远不能经常见面,但是每到虫季,自己总是想起那位远在南通的“忘年交”。讲情谊,重缘分,是斗蟋社会中的一个原则。
关系连带中的“利他”与“利己”
斗蟋社会中的“利他主义”与社会关系交往中强调资源交换的对等相呼应。社会中关系的对等不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因为这期间交换的不是外在于人的商品,而是依附并内在于人自身的很多东西——情谊、情感、物品(家传或者自己喜欢主观认为适合的)、面子、帮助等都可以成为交换的对象,但这种“交换”不是目的本身,人与人也不是单纯的商品和契约关系。交往始终围绕作为一个赫然独立于世间的独特生命体而展开。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市场定义为人在现代社会展开交往的主要场域,而把建立在算计理性基础上的利己主义作为交往的起点。当它这样做的时候,首先硬生生地把人从社会中拖了出来,把他塞入了市场;其次是把人的完整性割裂了,而把作为手段的商品交换当成了人关系建立的目的。
实际上,斗蟋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一样,人们交往的起点是利他,交往的目的是通过相互的利他建立一种平衡的社会关系,最终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性——而非简单物质和商品性——的“互惠”。关系总是由一个想和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并能“同情”地理解另外一个人也愿意与之建立关系的人发起。由此,发起人自然不能想着——在实际中也不可能——从对方那里先得到些什么,他总是会以“利他”的行为表明自己的意愿,对方如果有同样的意愿,必然也会回以某种“利他”的行为,从而让双方的关系发展出第一个平衡的支点。一位叫“权哥”的斗蟋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现在年轻人玩蟋蟀的少了,我们这一代(50~60岁)人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现代年轻人活得轻松,考虑的事情少。但实际上生活在社会中怎么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呢?谁不想从别人那里多拿点儿,但关键是别人也是这么想的啊。同样道理,我们为别人着想,多为人家做一点,社会上的人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肯定也要别人为自己贡献些什么作为回报的。以斗蟋蟀为例,我不可能和一个对蟋蟀一窍不通的人一起玩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相互的合作和贡献。即使在团队里,每个人必须要有对团队的价值,否则这个团队成员迟早会出现不和。我不可能让一个人老在我的虫(蟋蟀)身上押花挣钱。他有了好虫也要考虑我。第一次、第二次我都让一个人押花挣钱了,但到了他出好虫时却让我靠边站了,这样的人我以后肯定不会搭理的。这个圈子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总的原则是不能太自私。
笔者听完这位“权哥”的话感到很吃惊,因为这分明就是涂尔干在《劳动分工论》中要表达的思想。这位“权哥”不可能阅读涂尔干,但是他的观点和涂尔干这么相似,说明他们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立足于人性和社会交往基本原则的社会事实。
上海两个人,合作了将近20年,他们的特点是一穷一富。一个人不工作 ,平日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来源,但是对蟋蟀的甄别和饲养、出斗都很有经验;而另一位自己做生意,玩蟋蟀尽管也有20多年,但因为自己工作(或者是悟性)的原因,技术不如前面那位专业。他们每年都一起去山东收蟋蟀,经商那位负责所有的费用,两个人收的蟋蟀统一放在比较穷的那位那里饲养。当笔者问及他们何以能这么长时间保持亲密关系的时候,那位负责饲养蟋蟀的上海人很坦率:
因为我们都喜欢斗蟋蟀啊,都喜欢这种游戏啊。他做生意,到了虫季他是会放下手头的生意一定要去山东的,否则的话他一年都会感觉不舒服。我也是啊。我们就是规规矩矩按照玩蟋蟀的游戏规则玩。我们之间以及和斗场上的任何人不耍阴谋诡计。我们从来不玩“药水虫”。我们相互认可对方的人品,相互信任。这就是我们能20多年在一起的原因。
斗蟋社会围绕着蟋蟀和斗蟋蟀千百年来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的背后有社会行为原则的支撑。通过一种社会性嬉戏,斗蟋滋养并培育着嬉戏于其中之人的公民品格。
▲上文摘自《隐遁的社会》第三章:《“隐遁社会”之微观叙事及其逻辑》,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