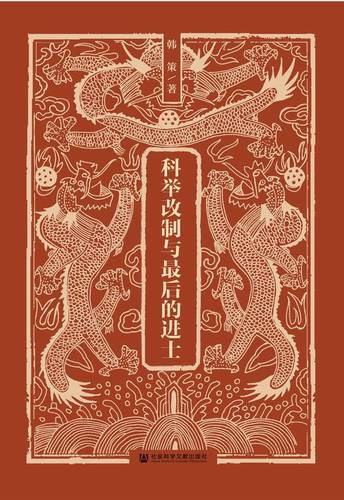陆胤|近代史的骨与肉
作者: 陆胤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7-12-11
编者按
本文为《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书评。部分发表于2017年12月3日《南方都市报》,作者授权本公号全文刊发。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一
读博时在历史系蹭课,时而看到一个让人疑惑的身影:面相老成如访问学者,执礼甚恭却仍是学生模样。若干年以后,才知道那是韩策,当初毅然从法学转入近代史,目前则是北大历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新书《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颇得史学界前辈的好评。
韩策是尚小明教授的学生,从留日学生、学人幕府,再到民国以来大学教员,尚教授多年来专力于士人群体研究,形成了一套综合人物行迹与量化统计的独到方法。韩策选择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是得自师传。癸、甲进士是中国漫长科举史上最后两科会试的成果,但其意义决不止于“最后”。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自辛丑(1901)科举改制的“策论举人”,实为戊戌以来朝野不断争论科举改章的产物。
科举改章废八股考策论,扩大了举子的知识范围。而成为进士以后,翰林院和六部的改革,进士馆的设立,进士留学的派遣,又进一步补强了这批最后进士的“新学”背景,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迥异于此前正途士大夫的进身之路。他们之间既是科举同年,也是新学堂(进士馆)的同学,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政学共同体。从后往前看,无论在科举史还是士大夫身份认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清末的官制改革、学制改创、预备立宪,为癸、甲这两科最后的进士拓展了迅速上升的途径,一改清中叶以来官场的拥堵局面。而随后辛亥革命的勃发,又使其出路严重分化。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如汤化龙、谭延闿、沈钧如、袁嘉穀、陈黼宸等,在民初政坛、法律界、文教界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往后看,清季最后两科科举所奠定的人际关系,在民国史上依旧影响深远。
韩策的新著所关注的,正是这批介于新、旧之间的“最后的进士”。众所知,“进士”是科举考试所能获得的最高身份,故从士的功名背景来讲,也可称其为“最后的士大夫”。这一选题和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其实颇具针对性。近年近代史研究界受外来新风鼓舞,颇张扬社会史、地方史、基层史等新视野;韩策此书讲的却是活跃于京城的士人精英,偏于梁启超以降新史学所不屑的“帝王将相”。其次,就晚清科举改制研究的小范围来讲,“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第16页);韩策则更关注文教变革在中枢发动的机制,在制度史的基础上还原“活生生的参与者”,可谓有骨有肉。
二
中国诗学素有以身体比拟诗体的传统。明人胡应麟《诗薮》有云:“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其实“史之美善”也可作如是观。韩策此书便可称“骨肉停匀”,既关注“活生生的参与者”,又以制度和机构为骨干。
近来颇有学者忧心史学研究中“人的隐退”。数十年来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理论方法纷至沓来,强调整体趋势、结构、量化、长时段,带来种种启示之馀,其末流却未免有汩没情性之虞。特别在近代史时段内,材料多、头绪繁、数据样本大,制度变化频繁,除了少数几个大人物,多数人的个体命运在历史潮流中宛如沧海一粟,或仅充当所谓计量史学中的一个数字而已。遂使近年的许多近代史研究著作越来越偏社会科学,而日益远离人文性。这在我一个中文系出身而对近代史有兴趣的外行看来,诚为遗憾之事。我们或许该追问: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没有人、没有温度的史学有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固有的文史传统,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中,还有无容身之地?
了解这样一个背景,就会看到从尚小明教授到韩策,多年来致力于士人群体研究的意义。这些士人群体是近代史庞杂表象背后的精神所寄,他们有理想,有情感,有身份认同的自负(如韩策书中所举,翰林在进士馆中不服留学生教习的例子),也有个人的小算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在科举展期争论中的算计),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尚教授和韩策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不动声色当中,用扎实的考证、辨析和细节的呈现,延续着中国文史之学“把人作中心”(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的作派。
但是,人物研究不是写传记,人物群体研究更不是写群传,专业史学还要有一套身手。1960年代西方史学界提出“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最初仍重定量分析,相对漠视具体人的存在。近百年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到人物“史迹集团”的研究法,须以一个中心人物聚集人物关系。然而,韩策所研究的进士群体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最后进士”的特殊性,是戊戌以来制度变革赋予的,要给这些血肉找到骨架,还是要回到制度史。所以他向前追溯科举新章的形成,作为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延伸,接上了一个庞大且专门的研究领域;向后则以进士馆为中心考察进士的“新学”教育,又是近代教育史上新学制、新学堂的内容。具体人在制度和机构中生活,强调人物中心,并不是否定社会结构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韩策对制度框架的研讨又非静态。制度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和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晚清这么一个巨变时代,制度和机构时时处于动态变化,少数关键人物的思量和交际,甚至可以影响制度走向,关乎多数人的命运。在本书前两章,韩策对于辛丑科举改制中借闱、展期和分场等具体问题,特别是其商讨、争论和最后定议的过程,都有详细的铺陈,呈现了制度背后人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角力。其中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在教育史叙述中甚为趋新的张百熙,竟上奏强烈反对科举展期,不惜化身保守朝官的代表,诘责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第29-34页)这类细节的呈现,或可打破关于晚清人物新旧归属的一些刻板印象。而张百熙与张之洞之间的龃龉,有可能影响到两年后二人在京共商学制和大学堂事务的过程,其间纷扰亦非“新旧之争”所能概括。
三
韩策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点,是精于史料辨析和阐释。
近代史研究史料猥多、体裁丰富、载体芜杂,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却对史料辨析提出了更高要求。近代以来流行的“平等看待史料”之说,其实甚有问题。史料从来就不平等,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史料的物质属性、载体、文体有别,都将造成阐释有效性的差异。与发掘新史料同等重要的,是还原史料的文献属性,辨析史料层次。
比如前些年研究界颇为看重的报刊材料,其意义就有待重审。韩策此书前两章探讨庚子以后的科举展期、借闱之争和奏定新章的过程,就指出先行研究存在着过分倚靠报刊资料的偏颇。他利用档案、电报、信札等更可凭信的一手材料,考出许多报刊载录之不可信。如辛丑年三月报刊盛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申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几乎众口一词,一些研究者也信以为真。韩策则在书中利用中枢与李鸿章往还电牍,证明李鸿章这一时期正为顺天山西等地乡试及北京会试努力交涉,不可能贸然奏请停考。(第40-41页)关于辛丑科举新章,以往研究也多从报刊钩沉,韩策则发现新章有众多版本,报刊所载之“八条”、“十二条”多有错漏,并非政务处与礼部会奏之“十三条”定本。(第50页)三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分歧,涉及拟题者、命题范围和命题标准。最终确立的章程中,由皇帝钦命的题目只有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包括《九通》内容。这些原则都跟报章所载有较大差异。
又如在科举史研究中,朱卷集成、乡试录、会试录向来是考察科场文字和衡文标准的重要材料,为研究者所爱用。而韩策却指出这些文献(特别是其序文)所标榜的原则和试卷本身往往多有差池,应该结合阅卷的实际情况来审查,以免为表面文字所欺;朱卷集成中的考官评语,也有事前事中事后等不同情况,且多属空谈,不足为训。就此而言,阅卷过程中产生的日记、书札等材料,反映了考官心态和科场惯例,透露出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反而更加重要。
韩策此书依据新出史料纠正先行研究误判之处甚多,却并不矜才使气。所谓“史料辨析”,不仅仅是辨伪(哪些史实说错了),更是梳理文献记载的层次。换言之,也就是历史真实的层次。比如报刊记载固然把史实意义上的真实弄错,却往往能表现了当时舆情的真实(如第106-112页所举进士馆的舆论反响),或者说是趋新派心态的一种真实,甚至可能是在放政治烟幕弹(第105页)。又如第151页指出“会试闱墨”普遍经过考官润色,固然不可当作考卷原样,却恰可看出考官眼光。所以,本书并没有因为依据了所谓“更一手”的史料,就把二手、三手材料一概抹消,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历史真实的不同版本与折射。每一次折射都有它独特的介质,其对最初事实的偏离,正可反映出介质的属性。其实何止是报刊,连笔记、小说、诗文集等文学性材料,都被韩策拿来驱使。这正体现了一个史家的技术,也是该书在史料学上特别予我启发之处。
此外,沿袭尚小明教授幕府研究的风格,韩策此书中载有大量表格和专业的定量统计。被他纳入统计的数据,多出于片段记载,一鳞半爪,散件于海量的档案、函电、题名录、诗文集等,需要很多联络、钩沉、拼接的工夫。但我所看重的,仍是韩策在数据面前的清醒。他注意统计方法的反省,更注重数据的分析,警惕过度分析。比如有学者根据癸、甲两科不同地区的中额,想要说明沿海与内地的风气差异,而面对内地少数省份中额较高的数据,又说这是人为调控的结果,结论先行,前后失据。相比之下,韩策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解读就要复杂得多。(第167页)
四
韩策此书虽以考证、辨析、统计见长,却不是东鳞西爪的碎片化研究。全书有严谨的结构设计,从变改科举这件事情的根源谈起,到庚子以后的乡会试的展期之争,然后才是科举新章的制定和实践,以及进士馆建制的原委。这些都是癸、甲进士这一群人——所谓最后的士大夫——能够产生的前提。往后则进一步论及进士馆的出路、留学,并按照翰林、部属、即用知县等类别统计他们在仕途上的分化,看到最后两科进士的前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黯淡;在有些层次上,他们的补缺、晋升,甚至改观了晚清官场拥堵的状况。
书末论及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之际的浮沉,许多现象值得深思。比如这两科进士因为知识结构较新,且在进士馆或留学期间接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所以其中的部属人员在辛亥以后多留任,与翰林的凄惨结局形成对照。但从清末学部到民初教育部的转型却是一个特例,学部—教育部在鼎革前后的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这或许体现出文教事业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联,即便在学部、教育部这样导入科层制的近代新部门中,亦未曾消解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缠绕。(第305页)
最后,作者还勇于尝试在史实基础上总结一些“模式”。比如论及清末科举由“渐废”转为“立废”的过程,韩策提出了“交互激进”的模式。(第83页)最初,只是袁世凯提出“增实科”,同时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改革后科举的新旧学对半开,旧额最终仍可保留。孰料号称老成的张之洞更为激进,声言“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袁世凯随即提出“渐废”旧额。下及1903-04年的三科递减方案,直至1905年的立停科举,都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陶模、端方等督抚之间竞相以趋新为政绩,“交互激进”而使变革加速度不断飙升的结果。对这一模式的总结,不仅可以阐释清末科举由改而废的机理,更可推而广之,用以观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
2017年11月29日于丰台花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