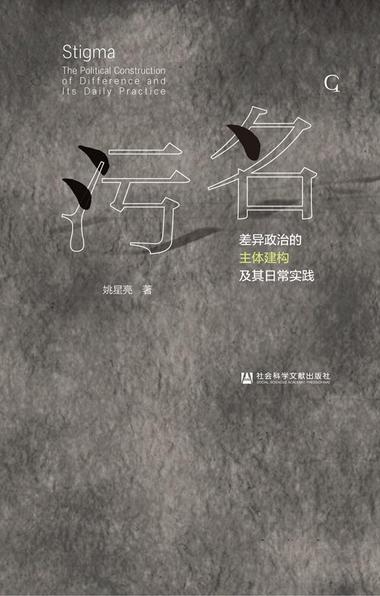污名的主体建构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7-06-23
Ⅰ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感知,譬如,“罗马数字1”“英文字母I”“矩形”,等等。但是当我们刚张嘴想说出来,又往往会突然觉得不对,因为想到了别的可能。为什么第1秒,第5秒……我们对它的认识会不一样呢?情况往往是这样的,第1秒对它有一种认识,稍一想我们又有了第二种认识,再一想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确定的认识了,你发现你想到了七八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是什么”,或者你也听到了其他人说出的七八种“它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意识到很难来界定这个对象——它是什么?那么,对于它“是什么”,我们到底能否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呢?
罗马人有话说
如果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我们又不禁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认识差异会这么大呢?为什么即便是自己,在不同时间段对它的认识也存在诸多不同呢?
再进一步想,既然对于一个如此简单、静态的对象都有这么多的认知分歧,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历史的、情境的、动态的、交织的……),真的有确定无疑的“是什么”吗?(而就社会科学来说,作为研究者,又真的能“发现”那个“确定无疑之是”吗?)
当我们开始有了这一层意识时,问题也接踵而至,这些认知分歧,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想想那些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冲突,极端到种族清洗的大屠杀,追根究底莫不是源于各种认知分歧。细思极恐,不寒而栗!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也不是几百个信徒或追随者能做到的。是什么凝聚了他们的共识,又是什么使得他们的共识得以践行?——那么训练有素,那么冷酷无情,那么长时间地执行这么一项残忍血腥的任务。而且类似的极端事件,绝不只是一两次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长河中,屡屡上演!
试图弄清这点,需要我们首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Ⅰ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又会在某些认识上达成共识?
希特勒
要回答这个“是什么”,换一个概念而言,即是“真相”。那么,第一,到底有没有真相?第二,如果有,那么什么才是真相;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认识所对应的是什么?
在语言学和现象学研究领域,已经有诸多研究者对此做出了细致的解析和论述。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从发生学角度而言,从认知论而言,而对于认知的差异及其日常实践,尤其是对于人与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主体(个体、群体、社会……)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认知机制与认知差异问题上,胡塞尔做出了突破性的重要贡献,指出了认知对象的二重性:实在性与意向性。简而言之,一方面,实在性制约着认知意向;另一方面,意向性界定着对于实在的认知。结合语言学概念来理解,实在性对应着能指,意向性对应着所指。索绪尔所谓的“能指大于所指”对应着实在性对意向性的制约;拉康所谓的“所指大于能指”对应着意向性对实在性的建构。实在性是共识的基础,而意向性则是认知差异之源。譬如,用来盛水的容器,其实在性制约着我们对它的认知,通常称其为杯子、碗或者盆等,而不会是刀枪剑戟;但意向性不仅仅造成了我们将其称为杯子、碗或者盆的认知差异,还会导致我们将其界定为武器(譬如用来敲击侵犯者的脑袋时)。换句话说,对象既是实存的,又是被建构的——其“存在”是一种意向性的即时存在,借用海德格尔的概念,是“to be”或者“being”(去存在)。其“存在”之真相,是由无数且无尽的不同意向性的“即时之在”所共同构建起来的。因此,对象“是什么”之真相确乎其有,但我们所能知者唯有构建真相的“即时之在”(真相之某个/某些面向),愈多则愈趋近于真相——然而,无以穷尽(就此而言,任何认知主体都只能是井底之蛙)。也因此,从人与社会的研究角度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对象的实在性,而是意向性及其“即时之在”——为什么如此存在,又是如何得以存在的?回到前面的问题,也即,为什么对象认知存有差异,为什么某些认知会形成共识,乃至取得垄断性的地位。归根结底,在于意向性,而意向性根源于主体的主体性。
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晰起来。所谓差异并非本质性的,而是关于对象的不同认知建构与认同(当用来敲击脑袋时,则同“是武器”,而不存在“是杯子”或“是碗”之意向性差异,同时,“杯子”与“碗”之实在性差异也变得无关紧要了)。
就认知建构而言,离不开主体的意向性。之所以说其是“罗马数字1”,而不是“罗马数字2”,一方面受制于对象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来源于我们既有的罗马数字知识库——从来不知道罗马数字的人,不会说其是罗马数字“1”;知道罗马数字的人,则不会说其是“2”。就此对象而言,罗马数字就是对其的一种知识建构,英文字母是另一种知识建构,等等。而之所以有的人的第一感知是罗马数字“1”,而有的人的第一感知是英文字母“I”,是因为主体的不同意向性——譬如,如果认知主体是个罗马人或者正在上罗马文化课,见到这个图示往往第一感知会是罗马数字;而如果认知主体正在上英文课,则第一感知往往会是英文字母;如果认知主体是个每天送快递的,则第一感知可能就会是一截黑色胶带了。可见,意向性的认知,既受到对象实在性的制约,又受到不同认知主体既有知识库或经验的影响,同时还是情境中的即时性认知。
由于我们对对象的认知是意向性的,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个对象就是一个意向客体,是被我们的认知建构而成的“存在者”。不同的认知意向,建构了对象的不同“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所建构出来的是什么呢?不是客体,而是客体的“特定存在”——它是主体与客体共同形成的一种关系事实,是客体的“此在”。就此而言,我们对对象的不同认知(对于“此在”的建构),当是完全对等的,不存在优劣高低之分,只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同时,现实中,我们经常经验到的对于某个对象的认识,往往是被某种认识主导的,其实质并不在于认知本身,而在于主体基于意向性的临时认同或共识。
哈姆雷特有新烦恼
那么,问题是,意向性的临时认同或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对于如此静态、简单的对象来说,比较好理解,多是由于认知主体有着共享的知识库、共享的情境,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意向性认知。但对于动态的、历时性的、复杂的、主体化的认知对象,譬如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等,认知差异更为纷繁复杂且往往变幻不定,但为什么也会形成相对集中的认同或共识呢?换句话说,在如此纷繁各异的认知中,某种认知如何可能脱颖而出,占据主导性乃至垄断性地位呢?尤其,就社会事件、社会问题而言,不同认知往往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关乎主体的切身利益,认知主体怎么能轻易舍己就人呢?这绝不会仅仅是有着共享的知识库或情境就能促成的,必是有着其他外在性的影响——不妨概况为:认知跟从和认知屈从。
认知跟从,相对比较显见,是认知竞争的结果。不同认知主体处于对等的地位,提供了各自的主体认知,一方面,有着相似背景知识或认知经验的主体产生认知共鸣而形成基本共识,如果达成某一共识的主体占据大多数,则其凝聚的共识会趋于主流而被标榜为“真相”,从而引领其他认知主体“弃暗投明”;另一方面,不同认知都会呈现出其合理性和解释力,在此占据优势的认知会具有相应的说服力和凝聚力,导致其他认知相形见绌,从而以“真相”自诩。认知跟从的另一个情况,是基于对某个认知主体的跟从而形成的——对其权威身份的认同或崇拜,而移情到对其所有认知的认同与盲从。
认知屈从则比较隐秘,是权力操控的结果。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限制其他认知参与竞争的途径;二是限制其他主体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第一种途径,最直接粗暴的就是禁言和审查。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为达到此目的的衍生手段和相对隐蔽温和的方式。第二种途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屏蔽信息的获取,以及更为常见的对信息的遮蔽、筛选、篡改,等等。同时,既然能够对这两种途径实施操控,那么相应地也会通过强化使其所主导的认知得以宣扬和贯彻,从而形成无以争锋的“真相”。
一旦取得垄断性的真相地位,该认知就会不断凝结为社会共识和社会记忆,或者糅合到社会文化之中,并对其他认知产生关联性或辐射性的影响,然后,通过社会学习等社会化方式,而得以强化与续延。
概而言之,真相既存在又不存在,既可知又不可知。真相存在,对应的是对象的实在性;而不存在,对应的是对象的意向性。存在而可知的是认知主体的意向性。对象的意向性,则涵盖着任何可能的认知主体的意向建构,因此不可尽知,不存在真相。真相可知,指的是构建真相的既有面向是可知的;而不可知,指的是构建真相的面向之多难以尽知。那么对真相的追求,只有两种路径:一是还原,通过对构建真相的某个面向进行还原,从而探寻其可能的本体;二是拓展,通过对构建真相的不同面向进行比较,从而归结出其可能的本体。
就研究来说,首先就是要寻找多重事实/现象,以此为抓手,通过对所调查的对象之面向,基于上述两种路径去探究真相。由前述可知,认知是主体意向性建构的,所谓事实当然也就是基于对象实在性的某个面向建构的了,它是一种关系事实。而真相就是由这些关系事实组成的,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事实越多,真相度就越高。但真相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虽然我们的研究目标在于真相,但研究重点应在于事实。追求真相的突破口,就是要寻找为什么某些事实会取得独霸性的地位,僭越为真相。
福柯
通过“路西法效应”,我们不免会生出这样的疑惑——到底什么是“主体”。主体,对应于英文的subject,法语的sujet,就其词源来说既有“主体”之意,也有“臣民”“臣属”之意。福柯在使用sujet一词时即强调了对“臣属”——受控制和管制特质的关注。彼特·丢斯(Peter Dews)也指出:福柯认为,任何自主性或自我决定论都应当被抛弃,因为这些理论的基础是“自由主体”,而自由主体从本质上而言是他律的,是由权力所构成的。从这一点来理解,主体的主体性,有着“被主体性”“被代理”的内在特性,也即有我们后文所强调的社会性。
笔者认为,所谓“完全主体性”是一个虚拟的幻象,因为只有社会的人才能超越自然的身体,而走向身体与主体的融合;也正是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待人,人才是“主体”,才具有主体性。主体建构是内化了的社会建构并在社会建构背景和相应情境中的再建构。太多的哲学玄思与纠结,并无益于我们对人之主体的理解。莫不如,我们干脆首先摒除主体之神秘的超然性,而将其界定为一般性的存在。主体并不局限于人的特指,任何具备主体性的实体皆为相应主体。因此,有待我们重新认识和澄清的首要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主体性”。
不妨认为,主体性,是对通俗而言的“建构”的抽象概括,但凡具备建构能力、起到建构作用的实体即为相应主体。譬如,语言作为一种实体,具备建构我们的认知、思考的作用,是为语言的主体性,由此成为相应的语言主体;社会作为一种实体,具备建构我们的交往与行动的作用,是为社会的主体性,由此成为相应的社会主体;而某个人作为一种个体之实体,一旦死亡,就不能再参与建构,由此丧失了主体性,也就不能再称其为主体。
因此,只存在“情境主体”——其实质上是一种关系主体——也就是说,是主体性建构了主体,并赋予和确立了主体的存在。主体当从属于主体性,而非相反!主体是主体性的客体,主体只在主体性践行的关系中存在,因主体性而存在——诚如叔本华所言:“客体开始处便是主体的终结点。”
同样,主体是否具备完全主体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成为一个伪命题了,因为怎样的主体性就确立怎样的主体。
来自叔本华的问候
虽然不同实体的建构能力和作用千差万别,但主体性是对建构力的抽象概括,因此主体性及其主体应当是对等的。然而,具体到特定的情景与关系中,所要求的往往只是某个或某些建构能力,从而造成了现实中的建构能力的局限和建构作用发挥的有限,导致了不同实体其主体性参与的失衡,以及相应的主体不平等。
在特定情境中,主体性得以施展的现实强弱决定了相应主体之间的地位优劣。作为抽象的主体性,在特定情境中,对应着相应的现实建构作用,是由所有卷入实体所共同制约的,是为主体间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主体间性只是主体性的局部,但却是特定情境中真正起作用的主体性,因此毫无疑问,主体间性优于主体性,并直接关联着相应的主体。从而,真正确立主体及其地位的,正是主体间性,而非主体性。由此可见,第一,主体的不平等是情境性的;第二,主体的不平等是主体间性作用的结果。
与污名所对应的问题,往往都是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对于敏感问题的认识、研究与分析皆会由此而变得更为困难。个中缘由,最为重要而突出的就是主体建构的问题。既包括其中所存在的对象之主体建构,更有着因为缺乏足够的主体建构意识而导致的认知问题和研究困境。
因此,对于敏感问题的研究而言,是否具备“主体建构”意识,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直接关乎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就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重要的不是能否有幸遇到一些能跟自己推心置腹的调研对象,而是如何识别和处理——不需要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些“为你准备的信息”,需要的时候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获取其他信息。
譬如在对我国西北地区从事性交易“小姐”的调查中,我们就发现,通常无论是老板还是小姐,在面对外人的质询、好奇,或者关心都早已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由辛酸故事、曲折经历、坚贞情感、道德信念、理想追求等构成的话语系统,这些无论在她们心里还是在现实中都可能演练过无数遍了。笔者及研究所的学生们在以前的调研中甚至还遇到过一些“访谈专业户”(“学术兴盛”而促发的频繁调研,让一些被访者发现了新的就业机会,他们转而积极地参与各种调研,通过迎合对方的需要挣取访谈报酬,为得到更多的报酬和机会他们不断积累相应的策略、技巧和动人的故事)。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曾从后台的角度提到过言及他人类似的现象——“缺席对待”,虽既有有意言及也有无意言及的现象,但都假设后台的言说与主体的真实认识或想法相一致(或者说,至少跟前台相比更为一致)。而我们所需要考察的恰恰是这种言及他人的言说(主体建构)在前台所呈现的情形及其不一致性。出于对调研方法的考虑,我们同时对性产业的周边环境和周边人员进行了考察,从他们/她们的角度来丰富对“小姐”的整体性认识。选择以歌厅老板为切入点,旨意不仅在于此,更在于研究取向的突破——以老板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她们对“小姐”的言说为文本进行分析——把这种言说还原到相应的情景、情境中,以老板与“小姐”的关系为主轴,分析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老板是如何建构“小姐”的,如此建构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老板的建构和关于“小姐”的言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呈现出不一致。
《污名:差异政治的主体建构及其日常实践》作者姚星亮
对于“真实”,主体建构强调主体性和情景,反对本质主义的真实观,认为只存在建构的真实。此处多次强调了“建构的真实”。胡塞尔的“意向对象”从现象学的理论视角所论述的也即真实性的主体建构问题,譬如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老板对小姐的认识和想法,是主体在一定情景下的建构,相对于这个情景和建构,这种认识就老板而言是真实的。但外界/研究者所能获悉和赖以分析的至多是“主体建构的情景”“呈现的情境”“呈现的过程、形式与内容”,从中窥视、探究原本“真实的主体建构”和建构背后可能的广阔现实。老板作为社会化了的人,在每个方面都有着社会的烙印——社会建构关于社会对个人的作用可参考;但同时也有主体的参与,从而形成了其个体独特的存在及视角——主体建构。潘绥铭和黄盈盈曾从“性”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主体建构的视角及其意义,老板对小姐的认识,就老板而言,是基于老板的立场和主体建构的视角,主要涉及这样几个要素:老板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老板所感知和了解的对小姐的社会建构、老板的个人立场以及和小姐的关系。这其中,主体的社会化程度和认识能力在短期内是稳定的;主体感知的社会建构是相对稳定的;主体建构对社会建构的再建构则是情景性的。在《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社区问题的一项社会学考察》的研究中,埃利亚斯和斯科特森曾敏锐地指出,闲言碎语的制造和传播是一个信息选择的过程。对于他群,人们往往尽可能选取其最坏的并加以放大,即力图对他群的形象贬损化;而对于我群,则是尽可能选取最好的并加以放大,即努力美化我群的形象。
因此主体建构的呈现则又是另一回事,不仅是情境性的,也是动态的——主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对先前的主体建构进行即时重建(对应情景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不大),并在当下的交往互动中基于自我呈现的考虑而相应地呈现出来(这时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第一,呈现时的主体建构已不完全是先前的主体建构;第二,呈现出的主体建构也完全不是新的即时重建的主体建构,而是当下情境中修饰了的,修饰的原因则在于对自我呈现的考虑——呈现成什么样会对自己比较有利,或者可以达到相应的目的——是一种情境性的动态策略。
如果对主体建构的一般机制略作归纳,则会发现:当社会建构呈贬抑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对外呈顺向强化建构;而当社会建构呈褒扬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强化建构,对外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此处所谓对内、对外,是主体自我认同的划分,譬如当涉及歌厅经营与利益时,老板就认同小姐为一体的而予以维护(弱化贬抑建构、强化褒扬建构);但在道德立场上,老板则刻意将自己与小姐区分开来,小姐也就被认同为外人而遭到贬斥(强化贬抑建构、弱化褒扬建构)和污名化。
可见,由于主流社会对性服务、性产业多有贬抑,老板们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涉足其间都难免会受到社会相应的贬斥/污名化,也承受了很多心理和现实压力,因此除了强调自己的道德形象和主流立场外,还需要为自己的经营方式寻求合理化的解释,从而建构起一道道精神上的防护墙,以此来回应和化解社会对其可能或已然存在的贬抑性建构(既有现实的,也有老板想象的);同时,也需要兼顾言说的呈现可能给歌厅生意带来的种种影响。
在重重顾虑之下,老板的主体建构与言说,以及不同情境下的言说呈现出不一致或者矛盾也就在所难免了。也正因此,老板对性产业和小姐的主体建构与言说,表面上是一种“言及他人”,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建构的自我呈现;而且老板的建构、言说和自我呈现都无疑是以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为意向的,饱含着情境中随机应变的技巧与策略。
推荐阅读>>>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污名的既有认识往往局限于对缺陷和弱势的关注。一方面,将污名的源起归结到某种生理或心理的缺陷特质;另一方面,将污名的动机与维持简化为(政治上)强者对弱者的社会控制、排斥,或者(心理上)自我优越认同需求的下行比较,从而将污名纳入到一种强/弱或优/劣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中。导致此种境况的一个原因,在于对污名与歧视的强相关认识,使得人们过多地牵制于与歧视相应的严重污名及其具象,而忽视了污名本身更为重要的独立特性和根本诉求,从而对污名相比于歧视更为深远的影响熟视无睹。
现实中,污名的日常实践与呈现远比我们所抽离出来的认识复杂、丰富的多。污名的心理动因与日常实践,污名的效应与应对也超出了一般社会性学习或情境性互动的范畴。人类受制于“自然差异” (身体)的局限、“标准”建构(知识)的局限、认知(真相)的局限,以及自我维持(主体)的局限。因此,必须首先认识到这四重局限,并对此尝试作出相应的回答,或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