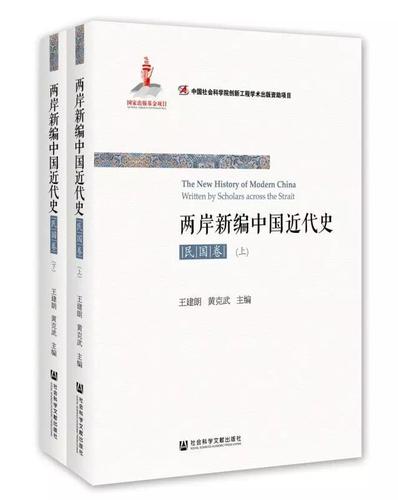忻平|民国城市居民的精神世界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6-12-29
编者按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的转型,城市居民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既冲突又并存的世界。作者从民风民俗、礼教、爱情与婚姻等方面展现近代城市中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本文出自《现代性与民国城市日常生活》,载《两岸新编近代中国史》民国卷。忻平,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国时期市民的精神世界受到现代性话语不同程度的浸染,已经距离传统愈行愈远。1913年的时候,孔子和孟子在一般读书人的心目中还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仅仅10年之后,在1923年底北京大学25周年校庆时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时,得到的答案已经完全不同。在国内人物中,10年前排名第一的孔子此时仅有1票,其他如庄周、王阳明等也各只有1票。孙文是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得票多很正常,连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得票,都远远超过孔孟等硕儒。国外偶像中列宁227票高居榜首,美国总统威尔逊51票,罗素24票,泰戈尔17票,马克思6票。这个结果表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击力,儒学独尊的地位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被严重动摇了。而列宁高居国外偶像的榜首,则说明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时尚。1923年4月,北京中国大学10周年纪念日进行的公民常识测验中,曾就中国的社会走向测问“你欢迎社会主义吗”和“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答案显示:欢迎社会主义者为2096票,不欢迎者为654票;欢迎资本主义者为736票,不欢迎者为1991票。
当然,现代性的势力范围总有其边界。黄公度对北平人力车夫的调查显示,在以革命为时尚的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无产者居然有半数不赞成革命。而他们正是革命要解放的对象。
另外一个例子是1932年有人撰文指出的:“如果我们不从统计上去考察,而仅就报纸新闻栏中的地位分配看去,那便会觉得婚姻与恋爱纠纷的数量,是占到所有社会纠纷的半部以上。”由此固然可以推测出,在二三十年代,婚姻和恋爱纠纷已成为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但如果从统计上去考察,情况就又不一样了。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当然要挖掘一些社会事件作为新闻,以致显得问题很严重。
再举一个例子,现代性崇尚科学,与科学格格不入的一些民间信仰自然也就被打入迷信一类。民国政府多次禁止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迷信活动。叶圣陶在小说《倪焕之》中描述过江南地区一次寻常规模的迎神赛会,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了解之同情:
一般人为了生活,皱着眉头,耐着性儿,使着力气,流着血汗,偶尔能得笑一笑、乐一乐,正是精神上的一服补剂。因为有这服补剂,才觉得继续努力下去还有意思,还有兴致。否则只作肚子的奴隶,即使不至于悲观厌世,也必感到人生的空虚。有些人说,乡村间的迎神演戏是迷信又糜费的事情,应该取缔。这是单看了一面的说法,照这个说法,似乎农民只该劳苦又劳苦,一刻不息,直到埋入坟墓为止。要知道迎一回神,演一场戏,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神,因而使他们再高兴地举起锄头。迷信果然;但不迷信而有同等功效的可以作为代替的娱乐又在哪里?
实际上,迎神赛会不仅“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神”,对城市居民亦然。从社会调查可知,城市居民用于迷信的消费占其杂费不小的比例,说明传统民间信仰与风俗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普通市民的头脑和日常生活中,因此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迎神赛会仍然屡禁不止。
风俗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处在人类一般精神生活的基础层”,往往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才形成的。其形成不易,变迁也难。但是在近代中国,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的转型,以及政府和知识界对移风易俗的鼓吹和倡导,民国城市居民的风俗也在变革。变政与变俗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关联。一些旧的习俗淡出了,一些新的习俗形成了。同时,在新旧交替和冲突中,更产生了许多变体。由于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主要集中在城市,民国城市的民风民俗变迁速度大大超过了乡村,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知识、文化和价值观诸多方面的断裂,结果使得“城里人”和“乡下人”两种认同逐渐得到了确立。
撇开城乡差异不谈,城市居民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既冲突又并存的世界。下面我们通过性、爱情与婚姻这一串主题来展现近代城市中传统与现代的纠葛。
在近代中国,关于性的话题大都与女性直接关联。这些话题包括了她们的衣着、身体、职业和社交活动。在这里,不妨从摩登女郎来谈起。1930年代的 《玲珑》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为《真正摩登女子》,向人们描述摩登女郎常用的标准:一是有相当的学问;二是在交际中能酬对,大方而不讨人厌;三是稍懂一点舞蹈;四是能管理家务。实际上这并不是当时主流视野中的摩登女郎,而更像是对女性的一种规范。就像电影《三个摩登女子》一样,导演意在重新为“摩登”定义,将爱国主义塞入其中,但这些努力并不成功。在二三十年代主流观念中的摩登女郎,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衣着的裸露。1936年,一幅《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的漫画以戏剧化手法描画、想象了未来女性成为上海统治力量的状况,她们将“从裸腿露肩的装扮进化到全体公开”,只是在“重要部分”系了一丝细带,而男性却仍然穿着传统的裤子,被解放了的她们称作“封建余孽”。难怪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特地对摩登女郎的穿着做了规定。
实际上,摩登并非是阔太太和富家千金的专利,就连都市中的年轻女工也开始崇尚这种 摩登生活,“一般年轻的女工,天刚亮就坐了车子去做工,一直到日落回来,生活尽管劳苦,可是姑娘们是喜欢效尤新装,夸奇斗胜,总不惜汗血去换一个表面”。城市女性的摩登化从学校女学生的变化也可见一斑,“与20世纪初期女校朴素踏实的校风不尽相同,二三十年代的女学生开始崇尚趋势和奢华了”。那么,这种时尚是如何形成的呢?广告的引导作用显而易见。重庆的《商务日报》就用广告文字描述了当时流行的女性装扮,如商业场华盛百货公司一份题为《妇女剪发之后》的广告称:
妇女剪发之后,须用头油头水梳光,再加压发圈压平然后美观,装束上也要考究才能配合,适会天气,正穿花样雅致、材料轻软、式样适体的短旗袍,至于跳舞长袜、高跟皮鞋也是不可少的,商业场华盛百货公司近到的各种化妆品、时新衣料及鞋袜等极合现时需要,欢迎赐顾参观。
实际上“女性符合美的每一个身体部位以及体现肉体美的装束,无一不靠消费来实现”。理想的女性是工商资产阶级“情欲的对象和商业利润实现的工具”。
再来看一看跳舞和舞厅问题。跳舞在1920年代末兴起,像穆时英这样的民国上海文人就经常流连于舞厅,并进行相关主题的文学创作。1928年,某报如此评述上海跳舞热潮:“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之春笋,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但跳舞也是一种涉性的东西,早在清末西舞输入中国时,孙宝瑄就曾从性的角度来观察它:
西国有跳舞之俗,类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国人鄙之,以为蛮野,不知彼盖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悦,乃发乎自然之感情,不可制也。而既非夫妇,则不能各遂其欲,必有郁结不能发纤者焉。惟听其行跳舞之仪,使凡爱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于以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岂非至道之极则乎?奈何薄之?
但孙宝瑄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实际情况是,那些舞厅的经营者往往要强化跳舞的色情一面。从下面这则上海歌舞厅广告即可知:“浓歌腻舞,现代的,艺术的,空前的,诱人的,自有真价,毋待吹嘘。群雌颜如玉,裸而歌,裸而舞,裸而撩拨人们的青春,妙乐似仙音,荡人魂,销人魄,感人的心,醉人的意。”措辞极尽诱惑之所能。这正是舞厅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跳舞和舞厅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其专业舞女的色情行为,也是因为跳舞中的男女接触引发了对“有伤风化”的担忧。1927年在天津曾经发生一起社会名流反对跳舞的事件。先是12位社会名流联名致函福禄林饭店股东,将跳舞与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再嫁、社交公开等新潮联系起来,指责跳舞是新思潮之体现,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之举,故坚决主张禁止。他们责骂跳舞是“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又说它“始犹借资游观,继则引诱中国青年女子,随波逐澜,是干柴烈火,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但报界很快就响起反对禁舞的声音。有人撰文将这些人讥讽为“遗老”。《大公报》发表题为《跳舞与礼教》的社评,对天津流行跳舞之风给予肯定,并指出跳舞与禁舞是一个社会问题。社评说:“天津今年忽流行跳舞。因而惹起反对,遂有福禄林饭店废止跳舞之事。然废者自废,兴者自兴,究竟跳舞应否禁废,礼教观念,如何维持,乃一种有兴味之社会问题,不仅天津所关已也。”
所谓的“礼教观念”,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一种性观念,也正因为舞厅与色情的过分结合,在民国的确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常成为被官方取缔的对象。官方的管理和禁止固然没有收到规范和禁绝的效果,但从郭卫东对瞽姬的研究案例可知,政府的干预如何影响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选择。瞽姬多指旧时从事演艺特别是在风月场中卖唱卖笑乃至卖身的青年盲女。此行当在旧时的广州等地兴盛一时,但也逐渐遭到各界抵制,在1930年代终至出现世风转移,部分盲女从此类行当中退出,“瞽姬”的名称也成为历史。但由于社会措施未能普适,部分盲女非但没有改变命运,反而因为中上阶层“公众兴趣”的转移而更加堕入“今不如昔”的境地。
性与恋爱在民国是一对纠缠不清的问题。五四后,自由恋爱观开始风行,而受西方影响,青年在处理恋爱与性的关系时,信奉灵与肉的结合。据苏雪林叙述:
五四后,男学生都想交结一个女朋友,那怕那个男生家中已有妻儿,也非交一个女朋友不可。初说彼此通信,用以切磋学问,调剂感情,乃是极纯洁的友谊,不过久而久之,友谊便不免变为恋爱了……贞操既属封建,应该打倒,男女同学随意乱来,班上女同学,多大肚罗汉现身,也无人以为耻。
据卢剑波说,吴稚晖曾讲过一个更极端的故事:“武汉某大集会上,男女杂众,突有一青年男子向一女郎的肩上一拍,说,‘我们交媾去’,迩时彼女郎面赧欲怒。青年男子便说,‘你思想落后了。’女郎闻之回嗔作喜,与青年男子携手而去。”在卢剑波本人看来,“假如当时男子确有性的切实要求而扳出道德面孔,加以抑遏,真是思想落后;受拍女郎尔时果自己有性的切实要求,或被引起了切实的性的要求,反而扳出贞洁面孔,加以抑遏,也是思想落后”。卢氏虽在文末声称“不主张过度性质的纵欲”,但其基本倾向已显而易见。
1928年,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马振华和汪世昌事件”。汪世昌是名军人,因对素不相识的马振华一见倾心,便写情书给她。马也对汪大为欣赏,称之“才貌兼全之奇男子”。两人诗文往来,大有古代才子佳人的意味,并在认识三个多月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汪世昌怀疑马振华已非处女,竟退还情书,表示决裂。马振华认为苦守的节操已被破坏,爱人又不再爱她,于是投水自杀。
事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马振华的婚前性行为是舆论界讨论的话题之一。有作者如此评价:“她的道德并没有坏,倘若社会不过因为她的被骗失身,就把失了贞操的罪名加上去,这就是错误的贞操观念;马女士受了骗,觉得无颜生存而自杀,也受了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作者从反对贞操观的角度出发间接支持了马振华的婚前性行为。但邹韬奋则表达了审慎的态度,说:“在女子方面,只要看所交的男友有不合理的生理上的要求,就是他百般言爱,但未有澈底了解而且正式结婚之前,遽有此要求,便是很危险的途径,应拿定主意,毅然拒绝。这一点如拿得定,就是发现对方靠不住,顾而之他,也不至于有何凄惨的结果……马振华女士之死于汪某,也是这一点没有拿得定所致。”邹韬奋的这一观念在当时拥有广泛的支持者。1930年的“叶冀熊劫杀孤孀案”进一步说明,传统伦理道德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非婚”为归宿的自由恋爱和性行为并不能得到社会认可。
作为自由恋爱的一事之两面,五四之后,婚姻自由观念也在青年中同步流行。二三十年代,时常有人以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婚姻问题的看法。1929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研究报告,在调查的181名已婚学生中,自己做主订婚的比父母代订的要多。被调查者中,凡自己做主或自己同意的婚事,婚后都比较满意;由父母或他人代定的婚事大半不令人满意。对于婚事不满意而想离婚的,占44.3%。总之五四以后,婚姻自由观念已深入青年一代的人心,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
不应忽视的是,婚姻自由观念存在着明显的代沟,其结果是大批的男性知识青年无法接受已成事实的包办婚姻,转而渴望通过自由恋爱获得理想伴侣。诸如鲁迅、胡适、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遭遇到类似的问题。1923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著名社会活动家陈望道述说了自己的婚姻历程:
我是一个曾经历过旧式婚姻痛苦的人。当我十五岁时,便被强迫结婚。因此,我十六岁入学校读书——以前是请人在家里教读——常住校中,不愿回家,校中教员、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极端用功的学生,其实不然,后来我觉得这样还不是根本的解决,非再走远一点,直到外国去不可。就一直在外国住了十年,除了父母生病及别的紧急不曾回家一次,他们以为我是用心求学,其实一半便是逃婚罢了。
婚姻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离婚自由。1921年在湖南任教的谢觉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男女解放之声浪盛,少年婚姻间所产生的苦痛益多,因知识之差异而害及感情,又以感情之无以维系而变生俄顷。此虽过渡时不免之现象,要亦当思救济之方,或顿变其主观而欢戚自异,或改良其客观而慰借自来也。”实际上民国时期的离婚问题得到不少的关注,其中离婚的原因受到了重点关注。上海市离婚率居民国各大城市之冠。上海市社会局发表的离婚统计材料表明,该市仅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两年半中,共有近2000件离婚案件,离婚原因首先以意见不合占大多数,行为不端为其次,在这些离婚案中,双方同意者占大多数,女方主动者有一部分,男方主动者不过百分之一二。
据天津《大公报》统计分析:“本埠最近三年来离婚之案件,原因不一,而大多数不外两种:一为逼娼,一为虐待。从此可推知社会经济之影响,不仅波及于物质界,并精神界而占有矣。不仅男子之劳力等于商品之供给,即女性亦成为商品矣。夫女子再为男子所支配,女子既失其支配自身之能力,社会又不能充分收容女子为相当之服务,其结果遂流于卖性。而其最大原因,实由于女子教育之不普及,知识能力之薄弱,依赖性之养成。”1939年萧鼎瑛发表的《成都离婚案之分析》一文,对成都市1937—1938年计70件离婚案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法院判决书中所载,其中80%为妻子主动提出离婚的。
民国时期的许多社会调查表明,从观念层面言之,离婚已经被普遍接受。1928年《大公报》曾刊登关锡斌关于《婚姻问题调查的答案》,32位受访青年男女中仅有2人明确表示无法接受离婚,其他人则表示认同。如天津一名19岁的男性在调查问卷上写道:“我的婚姻是旧式婚姻,感情不和,毫无爱情,是不满意的,仇人似的,一点快乐也没有!婚姻是我们一生最有关系的,不应当拿金钱结合,不应当拿欺诈手段来结合!更不应当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结合!我们应当拿纯粹的爱情来结合!因为我们各自的终身快乐起见,一定要离婚。”一位22岁的男子说:“我对离婚很赞成,夫妻情投意合当然没有离婚的观念,若是不和睦,整天里不是相骂就是相打,你视我为眼中钉,我看你不顺眼,夫妻变成仇敌,不如各寻山头的好。”
随着离婚案例的增多,有些人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予以肯定。如《盛京时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离婚是“国人思想发展之结果,婚姻关系人一生之苦乐,形式上虽注重在伦理上之结合,而实际上尤须赖理性之调适,徒有伦理上死板生捱,生拉硬扯,未有不发生问题者。今则科学昌明,神权日衰,思想解放之花大开。离婚案件之增加,除非我们认为人类思想发展是不好事,因此非但不容反对,还当原谅,还当援助”。陈剑华在《大公报》“妇女与家庭”专栏发表《婚姻问题》一文指出:“你若不满意对方,实在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不如索性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宗旨离婚,这如快刀斩乱麻一般,是最痛快的法子。”